一、前言
明清两代,江南地域社会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才女群体的兴盛。一方面,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处于一个封建礼教强化的时期。因为女性主“内”,对于家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空间的秩序生产非常重要,所以江南地域社会一方面强调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三从四德,官方与民间都不遗余力地褒扬贞妇、节妇,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秩序,强调“内外有别”的空间秩序,在空间上将女性禁锢在家中;而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相当多的才女群体,强调女性个人的才华、性情,才女们结伴出游,与士人交往、唱和,在很大程度上越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规范约束。然而地域社会和其秩序维护者士绅群体对于才女群体的这种“越轨”,却持一种包容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鼓励姿态。
对于才女的文学交游,文学研究者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这类研究数量众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对才女群体的社会认知与接受,目前的研究甚少,仅许周鹣从吴地文化的特点予以了论述,然而这种论述也是从江南社会的文化习性来论述的,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心理层面。
明清两代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才女,既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域社会中其行为被容忍与接受,在社会心理层面,就意味着“才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社会认知的一部分,从而在与才女交往时,这一范畴才能被启动、激活,成为人们对才女的认知框架和行为图式。
在社会认知意义上,“才女”在当时对于江南社会的成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认知范畴,在人们与才女交往时,人们无法用已有的“女子”范畴中所包含的内容和社会性规范来与之交往,而必须在交往实践中发展出新的范畴,因而“才女”的群体范畴的定义也处于不断的修正争夺中。明清江南社会才女群体的出现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在认知层面,作为一个范畴群体,具有什么样的群体特征和刻板印象,这些群体特征和刻板印象是如何与中国社会中已有的女性范畴发生交集和冲突的?这些认知范畴中的交集和冲突又如何体现了才女自身和地域社会的精英在“才女为何”的定义上的权力争夺?进而,才女群体作为一个认知范畴被确定下来以后,对于地域社会的运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社会—心理问题在以往的才女研究中被忽视,本研究尝试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对这些问题做出历史社会学的回应,从而在视角和问题意识上丰富目前的才女研究领域,对于才女群体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复杂互构关系予以社会心理学的初步探讨。
明清虽有女学,然而其内容主要为修身养德,是对“三从四德”的强调。而才女们的“才”强调的却是性灵诗词的文才,在内容上是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而当时江南社会才女群体的兴起以及士林领袖对女才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混淆和动摇了“女学”的内涵,以至于史学大家章学诚因为不满袁枚等收女弟子而撰写《妇学》澄清两者的关系。
饰时髦之中驷,为闺合之绝尘,彼假藉以品题,或誉过其实,或改饰其文,不过怜其色也,无行文人其心不可问也。呜呼!己方以为才而眩之,人且以为色而怜之,不知其故而趋之。愚矣!微知其故而亦且趋之,愚之愚矣!女之佳称谓之静女,静则近于学矣。今之号才女者,何其动耶?何扰扰之甚耶噫!
章学诚的这番批评中有三个信息值得重视:第一,当时才女的标准主要是强调诗文的造诣。第二,当时才女们与男性文人交往很广泛、很活跃。第三,才女们往往有色。这三点与传统社会对“女子”这个社会认知范畴的社会规范性内容构成了不一致。传统社会对“女子”这个社会认知范畴的社会规范是:第一,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不能流动,家庭空间是女性主要活动的空间。第二,男女有别,女性除了家人外,不能外出与男性交往。第三,女性重妇德、妇工,为未来执掌家务、孝敬公婆做准备,为传统社会的上下义务性关系生产服务,而才、言、容等个体性的特征对女性来说并不重要。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章学诚笔下的“才女”所具有的特征与地域社会和家庭空间对“女子”的要求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动与静、才色与德、“才女”跟陌生男性交往与“女子”跟陌生男性隔离,“才女”在认知范畴上构成了与传统的“女子”的不一致,才女群体是一种与遵循传统社会秩序和规范要求的“女子”具有不一致性的新的女性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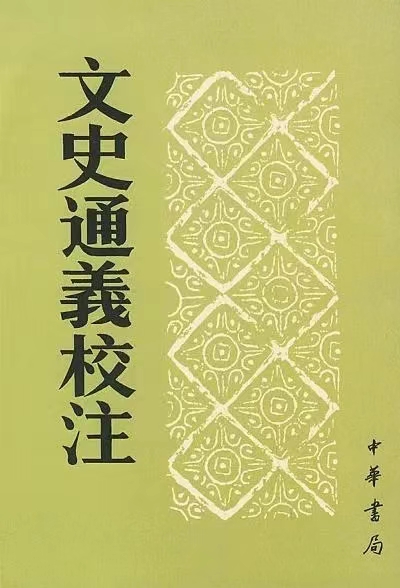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那么,章学诚对当时“才女”这种与社会空间对女性的秩序和规范的不一致性的概括与批评是否属实呢?明清时期江南的才女群体是否具有这种与其他“女子”之间的不一致性呢?如果是,这个新的群体范畴的代表项内容和与其他女性群体的群体边界究竟是什么呢?
二、个体性才华:“才女”与 “女子”的群体边界
在清代著名小说《儒林外史》中讲述了两个才女的故事。一个是道学式的才女鲁小姐。
他这个才女,又比寻常的才女不同。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做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
鲁小姐这个才女,精通的是八股文章。等到结婚,丈夫蘧公孙也是少年名士。一天,鲁小姐写了一行题目“身修而后家齐”,假托其父鲁编修的名义向公孙请教。“公孙接了,付之一笑,回说道:‘我于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经满月,要做两件雅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公孙心里只道说,向才女说这样话是极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讳。”强调鲁小姐与一般“才女”不同,很明显在公孙和一般舆论看来,对一般“才女”群体范畴的社会认知是“才女”擅长诗词而非制义以及儒学。
而书中另外一个才女沈琼枝,智勇过人,因被骗婚至盐商家做妾,她设法从盐商家逃出,上了船离开扬州。她细想:“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做两句诗,何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于是到了南京。在码头处设了招牌。“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挂了招牌,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托刺绣的。”后来盐商查找,杜琼枝到了县衙门。知县看她容貌不差。问道:“既是女流,为甚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沈琼枝讲清了盐商骗做妾的实情。知县道:“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请知县命题。知县指着堂前槐树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就暗中向江都县令说情,将沈琼枝开释了。
从公孙对鲁小姐制义的反应以及沈琼枝作诗可以看出,“才女”这个社会范畴在当时主要是指能诗词的女子,才女可以依靠自己的才学独立谋生,并与男性名流交往,而儒林和官府对于才女也另眼看待。这意味着才女可以凭借她的才学成为自食其力的个体而无须仰仗男性生活,甚至可以凭借才学改变自己的婚姻状况。在物理空间上游动而非固定在家庭空间之中,在关系意义上成为个体而非被束缚在义务性关系之中,才女强调个人的才学,可以与男性交往而非隔离,当沈琼枝被他人归类到“才女”这个范畴群体中时,作为一个才女的这些特点使得她成为与社会空间对“女子”的规范不一致的女性。
沈琼枝式的才女并非仅仅是小说家言。才女群体作为一个范畴群体,在社会认知层面具有与当时社会空间对女性的规范的不一致性,这就表现为才女群体的与其他女子的群体边界上。
才女群体与其他女子的首要区别是能诗词。与前代相比,清代士人对于女性的诗文之才是大加褒扬的。为才女填诗赋文辩护的最有力也是最普遍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充斥着大量的妇人之作和爱情之作。“古诗三千,圣人删存三百。妇女之作,十居三四”;而历代诗歌中均有女性作品。“夫四始流音,半采房帏之作;五言肇体,即传宫扇之吟……”;第二个理由就是男性在创作女性题材时的矫揉造作与不自然,这被清代强调诗文贵在自然、发于内心,天然去雕饰的“性灵论”大为批评。“强誉罗敷之媚,总涉浮辞;侈谈西子之妆,讵曾平视。探来芳信,莫须有之幽欢;误尽佳期,想当然之恨事。何如应浓应淡,自谱画眉;宜短宜长,亲填捣练;月当楼处,念奴面诉其娇;雨打窗时,蕃女口占其怨?”强调女性题材由女性来创作比男性更为自然和真实。
第三个理由是士人认为女性在诗词创作上,较之男性更有优势。“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而清初著名词人尤侗同样认为吟咏作词更适宜女性学习。“愚独谓韦母《周官》,大家《汉志》,宋尚宫《论语》,郑孺人《孝经》,未免女学究气,小窗工课,吟咏为宜,而诗馀一道,尤为合拍。”
在这种褒扬才女创作的思路下,男性士人认为女性创作诗词相对于男性创作而言,既是补充和附庸,但同时又有独特性无法被男性创作取代。“男子日也,女子月也。女子之文章,则月之皎极生华矣。……蟾光一片,可以继乌翼之余辉。”
应该看到,在“性灵论”的视角中,由于诗词的用典雕琢不再被视为诗词的主要标准,而语出自然成为新的标准,这对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男性的女性来说,有了和男性在诗文领域一争长短的可能。由于女性对心理感觉的敏锐捕捉和白描较之男性更为准确,而“性灵论”也使得女性无须引经据典,创作的门槛大为降低。上述为女性辩护的男性声音放置在“性灵论”统治清中期诗坛的背景下就不足为奇了。如有学者辩说女性生而宜诗词:“妇人之不可……无才也,譬之赞山,凝厚者固其质,……譬之赞水,澄私者是其性”,认为能诗词是才女的天性。而赵世杰更认为灵气独钟才女而非男子。“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
这种男性推崇女性在诗词创作上的优越论进而成为才女对自身群体边界的一种自觉认同,如才女陆卿子强调:“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才女甚至公开表达自己对自身个体性才华的认同,将之视为自身与一般女子的主要区别。王衡之女王氏“曾榜其室云‘金闺文作市,玉匣气成虹’”,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才女身份的自觉认同与自得之情。
苏州著名才女徐媛亦借《七夕》一诗将才女与一般女子的群体边界描绘了出来:“机丝隔断须抛掷”。才女为了诗词创作可以放弃女工这样家庭空间中的女性的主要象征物,从而将才女群体与一般女子的边界微妙地表达出来。
屠隆将这种才女的群体边界表达得更加清楚。“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筐,都无针线箱。”图书作为才女的身份表征,而针线成为普通女子的表征。才女通过诗词创作,成功地将自身变成了一个女子范畴的新类型——才女群体,这样的女性群体与社会空间对女性的规范要求不一致,个体性才华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的成员资格,从而为摆脱地域社会为女子贴上的标签和各种规训技术提供了心理和认知上的可能。
屠隆曾为其女儿与儿媳的诗文辑集出版,他认为对于才女而言,普通女子的表征物:女工并不适用。“刺凤描莺,并非其好;雕龙绣虎,各擅其长。吐词疾捷,二弟犹让神奇;秀句联翩,一时称为灵媛。”才女与普通女性甚至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不一致性首先就表现在拥有个体性的才华,这就使得才女群体与家庭对普通女性的空间规训要求相去甚远。

胡文楷(编):《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可见,才女的个体性才华已经成为才女群体成员自觉的社会认同,并且凭借这种认同,才女将自身视为与“女子”不一样的社会范畴,从而将自身与社会对普通女性的规范区分出来,社会对女性的规范要求主要体现在家庭这样的社会空间之中。一是三从,是强调女性对上下义务性关系的顺从,是去个体化;二是主持中馈,主内是物理与社会空间意义的固定与隔离,因而,德行和女工是实现这种对女性的空间固定与隔离的具体的规训技术。而才女则突破了女工这种规训技术对自身的限定,将女工归之为普通女性具有的特征,而利用自身的个体性才华将自身逸出于这一规训技术,从而拥有了与家庭空间秩序要求的不一致性,拥有了相对于社会其他女性成员的异质性,从而也就意味着“才女”作为一个范畴群体,在社会认知中与“女子”这个社会范畴出现了不一致性和异质性。这种认知意义的异质性就使得人们在认知才女群体时,无法直接调用头脑中已有的“女子”范畴来构成反应和行动预期,“才女”成为在认知上难以迅速形成分类和判断的对象,是认知上难以确定的陌生人,这种不确定性和陌生性,构成了对“女子”这个范畴背后的家庭秩序的威胁。
三、无德便是才还是才不碍德:“才女”社会范畴的定义争夺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攻击才女,认为女子的才与女子的德是对立的,才女的行动必须要被社会所规训和禁止,“才女”范畴与“女子”范畴的不一致性必须被消除。前述的章学诚的言论仅为当时的一例。
孙奇逢对于才女恃才从而越出社会对女性的“内”的空间边界限定做出了严厉的批评。“我闻之:‘妇人无才即是德’,近来妇人结社,拜客作诗,至男子为其妇兄才,持其诗献当道,求为刻传大家,称述以为韵事。吁嗟!此风浸淫不已,岂世终无阳刚大人,一洗此阴靡者乎?”而周亮工之父更是对才女进行了道德上的污名。“《列女》、《闺范》诸书,近日罕见;淫词丽语,触目而是,故宁可使人称其无才,不可使人称其无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诗章,不幸流传,必列于释子之后,倡妓之前,岂不可耻?”
社会秩序维护者感觉到了“才女”作为一个认知范畴给家庭空间秩序带来的威胁性,要求将才女放回至“女子”的社会范畴分类体系之中,强调对普通女性的家庭空间规训技术对于才女必须是同样有效的,从而否定才女的异质性,否认才女群体作为一个新的独立的与“女子”不同的群体范畴存在的可能性。
面对取消才女个体性才华所展现的异质性,将才女放回家庭空间从而消除这种异质性的规训要求,才女群体为维护自身异质性所使用的话语策略是将才女群体作为“女子”的一个亚范畴而非相对立的认知范畴来建构群体边界。这样,才女依然可以有个体性的才,但必须同时要有普通女性社会规范意义的女德。在接受了家庭空间对女性的普遍性的规训技术的同时,才女将自身归类为一个认知意义的亚类型,既具有与女性一样的普遍性:妇德,遵守家庭空间对自身的道德与社会规范的规训,同时还保留了才女群体作为一个亚群体自身的边界:妇才。通过个体性的才华而与其他女性和社会其他成员保持着异质性,进而保持着一定的社会距离。这样,在认知范畴中,虽然是一个亚范畴,但还是保持着与其他女子的范畴定义和行动预期的区别。
因而,“才女”群体边界的第二个要素是德行。才女不仅要能诗文,而且要有德。有德又有才,成为才女群体的主要成员资格和群体边界。
试举几例有才有德的才女。
张氏湖广黄冈人,工诗词。先是已字某,父悔将改字富商,女闻之引刀自刎死。
钱唐女子吴栢,字栢舟,未嫁而夫卒。栢缞麻往哭,遂不归母家。所著有栢舟集。
范满珠,范眉生妹,诗才与兄相称。集名绣蚀草。
山阴才女胡石兰,嫁骆氏早寡,为女学究,有名都下。
当个体性的才华与社会规范意义的妇德能够同时在才女群体身上合为一体时,才女作为一种新的女性范畴类型,就不是一种在认知分类体系中难以分类的陌生人,而是家庭空间秩序的维护者,是“女子”的一员。
监生陈应奎妻陆氏,襁褓中即能识字。比长涉猎经史,工诗,有才女之目。既归陈,事祖姑及舅姑温凊无亏。夫得瘵疾,氏刲股和药以进。夫殁,晨夕守灵帏。母徐年老多病,氏常归省,刲股者再。母殁,哀毁,亲制皮被于棺外。曰吾母晚年畏寒,不可不念也。见母所嗜物,不忍尝,年四十一卒。道光八年旌。
这样类似的才女有德的记录在笔记和地方志中是屡见不鲜。才女有德,从而与社会成员之间具有一致性而不是完全的异质性,在社会范畴中保证了自身符合“女子”范畴的社会规范性内容要求,是才女群体不被社会排斥的重要策略。然而,单单强调才女有德是不够的,因为家庭空间的秩序虽然是建立在妇德的基础上,但是妇才这样的个体性因素也会影响、削弱妇德这种强调去个体化的义务性关系伦理的秩序生产,从而家庭空间秩序的维护者对于才女的个体性才华也持反对的姿态。因而,要想一方面保留才女的才从而拥有异质性,另一方面又要让家庭空间能够容忍才女群体而非驱逐和污名,就必须要强调女才不仅不妨碍女德,而且相反,女才有助于女德这样的家庭空间秩序的运行和强化。
这就首先意味着,必须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进行新的话语解读,才能在家庭空间中寻找才女群体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让才女成为“女子”中的亚范畴而非难以确定的陌生人。
人亦有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盖以男子之有德者,或兼有才,而女子之有才者,未必有德也。虽然如此说,有才女岂反不如愚妇人?周之邑姜序于十乱,惟其才也。才何必为女子累,特患恃才妄作,使人叹为有才无德,为可惜耳。夫男子而才胜于德,犹不足称,乃若身为女子,秽德彰闻,虽夙具美才,创为韵事,传作佳话,总无足取。故有才之女,而能不自炫其才,是即德也;然女子之炫才,皆男子纵之之故,纵之使炫才,便如纵之使炫色矣。此在士庶之家且不可。
这段话的作者作为男性,意识到要想让地域社会趋于稳定,必须让女性安于家庭空间,让女性成为服从男性的上下义务性关系绑定的个体。因而家庭空间对女性的规训要求首先是女德,并认为女才确实对女德有着削弱的功能。但是作者认为,才女只要不炫才,不让个体性的才成为对家庭空间秩序的威胁,就是德了。很明显,作者感受到了才女的个体性的才华对于家庭空间秩序的危险性,并将对才女的规训要求降低,其德与一般女子的规训在程度上比是很低的,只要无害就可以。而一般女子则要做到妇德,即对家庭空间秩序的高度服从与认同。这事实上体现了对才女群体的一种认知上的调整与容忍,不再将才女视为“女子”范畴中的完全对应物来进行认知和行动预期,而是将才女群体视为是与一般女性不一样的群体,是有着异质性和社会距离的群体,对于这个新的群体,其认知框架和空间规训技术必须和普通女性不一样。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图片来源:搜狐网)
而才女群体自身则进一步提出了德才不碍的观点,以证明自身对家庭空间的无害性以及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例如明代才女梁小玉就直率地指出:“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
家庭空间秩序的维护者刘氏,在她编撰的《女范捷录·才德篇》中也强调:
“男子有德便是才”,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夫德以达才,才以成德,故女子之有德者,固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贵乎有德,德本而才末,固理之宜然,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它强调的是女德不必有才,这样普通女性依然必须接受家庭空间的规训,而女子有才必有德,则强调了才女作为女性的一个亚类型,具有与其他女性的一致性或者说是同质性。换句话说,德是家庭空间对才女与普通女性的共同要求,是所有女性都必须具有和遵守的,而才是才女群体的特性,作为异质性的才可以使得作为同质性的女德增强。这样通过强调女才对于女德起着促进而不是阻碍作用,将才女视为一种女性的亚类型而非新类型,才女就可以安然于家庭空间的秩序中,成为与其他女性拥有同质性的女性,虽然才女依然保留着其个体性的才,也就是保留着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不再是对家庭空间秩序的危害,而是对家庭空间秩序的强化,从而让家庭和社会可以容忍才女群体而不是将之驱逐和隔离。
才女夏伊兰在她的《偶成》篇中,更是将个体性的才有助于规范性的女德的培养和认同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独至评闺材,持论恒相反。
有德才可赅,有才德反损。无非亦无仪,动援古训典。
我意颇不然,此论殊褊浅。不见三百篇,妇作传匪鲜。
《葛覃》念父母,旋归忘路远。《柏舟》矢靡他,之死心不转。
自来篇什中,何非节孝选!妇言与妇功,德亦借此阐。
勿谓好名心,名媛亦不免。
对于女才与女德之间的正向关系,最有力的辩护武器莫过于《诗经》这部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关于女性的描写。华亭解元王献吉作为一个成功的男性士人,就曾对他的姐姐言道:
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关雎之求,卷耳之思,蠢斯之祥,柏舟之恋,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为化始。
将《诗经》这部儒家经典对女性有才的描述视为才女群体在地域社会与家庭空间中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从而抵御地域社会与家庭空间对才女群体的个体性才华的监控与反对。这样一来,才女就不是一个新的与普通女性不同的不受社会与家庭空间规训的、拥有异质性的、在社会认知中难以确定的陌生人,而恰恰相反,是社会与家庭空间的有力维护者,是可以被范畴化、预期其行动的社会成员。
才女顾若璞同样也是以《诗经》为武器来为“才女”这个新的群体范畴做辩护,她在给黄鸿的诗集序中表达了自己作为才女对于妇德的思考。
妇德兼妇言,古识之矣。卷耳之什,首列风人,未见踰节,柳絮单词,流耀千载。
顾强调才女是对社会无害并且有益的群体。才女不是与社会其他成员拥有不一致性和异质性的陌生人,而是和其他女性拥有同质性,是对于社会空间秩序生产至关重要的社会成员。
冯梦龙表达了类似的见解:
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
因而,有才并非无德,才有助于德成为才女群体用来反击家庭空间秩序维护者的主要观点,在这个范畴代表性的定义争夺过程中,德才兼备也成为“才女”社会范畴的主要内容和才女群体的群体边界。通过对德的强调,才女群体将自身所属的社会范畴成功地归类为女性群体中的一个亚类型,从而既不对家庭空间秩序带来威胁,又事实上保留了自身的个体性的才华,保留了自身拥有与家庭空间和地域社会其他“女子”异质性的事实。
四、德才兼备:“才女”范畴代表项的确定与地域社会的秩序生产
德才兼备作为当时才女群体的群体范畴内容和成员资格,我们在当时的评价中可窥一斑。皇甫司勋在给常熟程氏作的墓志铭中叙述了才女的标准:“幼秉淑姿,夙闲女诫,授以《孝经》、《列女传》,了悟大义,称闺秀焉。”可见有女才、有女德已经被时人视为(才女)闺秀的重要标准。
然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德才兼备的话语表面上看来是家庭空间对才女群体的一种规训技术,是从社会认知的层面将才女放置“女子”的范畴之内,试图将才女群体和普通女性一样禁锢在家庭空间之中,成为去个体化的服从上下义务性关系的个体,但是同时这也是才女群体自身的一种话语策略。通过这种策略,才女群体依然有效地保留了自身的异质性:个体性才华在家庭空间中的合法性,保留了才女群体和其他女性群体的群体边界和社会距离,从而成为家庭空间中的拥有异质性的陌生人。
这种异质性使得才女群体获得了其他女子没有的社会空间中的移动自由。这种自由一方面是指才女一定程度上在物理空间中的流动能力,相对于被禁锢与隔离在家庭空间中的一般女子而言,这是物理空间移动意义的自由,另一方面就是在社会空间意义的移动自由。如前所述,妇德这样一个对待普通女子非常严厉的道德与社会空间秩序,在对待才女群体时,就表现出了一定的宽松和弹性,并不完全按照对待普通女性的道德与社会规范来严格要求才女群体。
家庭空间在对待才女群体时,由于其已经开始接受才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与一般女子的不一致性,在认知框架和行为预期上对于其个体性和流动性均有一定的认知,因而不会运用对普通女性的规训技术来对待她,要求其绝对地服从上下义务性关系的生产,而是出现了一定的秩序弹性。如前引的《儒林外史》沈琼枝的故事。其实沈琼枝的事情是有蓝本的。见下引文:
女子无才便是徳。世人类言之,然能恪守闺箴,虽遇人不淑而无交谪之声,则才德兼备矣。盐城有才女者,不详其姓氏,嫁夫某,业儒家,贫甚而伉俪颇相得。届天中节,杼轴其空,几不能举火。女咏一诗云:“自怜薄命嫁穷夫,明日端阳件件无。佳节莫教虚过去,聊将清水洗菖蒲。”书于案头,夫见之殊自愧,忽怱去。明晨操豚蹄,酒一盂,以返邀妻大嚼。妻不解固诘之。笑不答。未数日,吏胥拘夫去。盖端阳酒肉之需,从邻家窃牛来也。县令诘责某,遂口诵妻诗。因逮女问曰:“汝既能诗,可面试乎。”女曰可。令遂以牛为题。女口占云:“滔滔黄水向东流,难洗今朝满面羞。自笑妾身非织女,夫君何事效牵牛。”令大加击节,遂赦其夫,为赎牛归之邻家,并给白镪二十金以济其贫。呜呼!令可谓风雅爱才者矣。若女也巧思天成,冰清玉洁,谓之才女也可,谓之贤妇也亦可。
盐城才女的故事让我们发现,才女一方面因为其异质性:个体性的才华而得到地域社会的认可,承认对待“才女”的认知和行为图式与普通“女子”不一样,从而使得社会空间秩序在规训才女时有一定的弹性和缝隙,但与此同时,她也必须首先是“女子”这一社会范畴的亚类型,拥有与社会其他女性成员的同质性,必须是贞女、德女,才与德不可对立,不能有才无德而是要有才有德、才德兼备,这样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合为一身的才女对于家庭空间秩序来说就不是威胁,相反她同时获得了家庭空间对她的容忍和某种程度的移动自由,即家庭空间的秩序:妇德对她来说不是僵硬的,而是有弹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才女群体在围绕才女为何的话语争夺过程中,逐渐建构成“才女”是一个与“女子”这样的范畴群体既拥有异质性又拥有同质性的群体。在面对家庭空间的规训时,第一种策略是强调妇德对于才女的变通性,才女群体在符合某种妇德的同时,无须遵守所有的妇德,妇德对于才女来说,是可变通的、有弹性的。这其实是强调家庭空间必须认可才女群体的异质性是其主要的群体特质,家庭空间必须对才女的异质性予以认可、容忍,才能换得才女群体对其自身同质性的认同。才女首先是在家庭空间中拥有异质性的个体,然后才是遵守家庭空间中上下义务性关系生产的社会成员。
而另外一种话语策略就是承认妇德是才女必须要遵守的,并且做出遵守的姿态,展现出驯服的意象。这其实在强调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同质性才是才女群体的主要特质。在这种驯服的意象中,才女成为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的服从于上下义务性关系生产的社会成员,才女群体不再对家庭空间秩序构成威胁。
梁孟昭谈到了这种驯服的意象:和社会其他成员的一致性和同质性给才女的异质性:个体性才华带来的困扰。“我辈闺阁诗,较风人墨客为难。诗人肆意山水,阅历既多,指斥事情,诵言无忌,故其发之声歌,多奇杰浩博之气。至闺阁则不然。足不踰阃阈,见不出乡邦,纵有所得,亦须得体。辞章放达,则伤大雅,朱淑真未免以此蒙讥,况下此者乎!即讽咏性情,亦不得恣意直言。必以绵缓蕴藉出之,然此又易流于弱。诗家以李、杜为极。李之轻脱奔放,杜之奇郁悲壮,是岂闺阁所宜耶!”安于家庭空间秩序,就意味着才女必须放弃其异质性展现的可能,在社会交往上将自身限定在家庭的边界之内,做一个遵守家庭空间秩序的女性,从而对于自身的异质性:个体性才华的发展带来了妨碍。德为先还是才为先构成了对“才女”认知图式中的启动因素,在这两种话语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对这种认知图式的启动因素的争夺,才女群体与江南地域社会之间的权力争夺。

《豳风十二月图说》之“十月获稻说”
(图片来源:书格网)
而相当多的才女为了实现这种家庭空间的秩序规训下驯服的才女意象,不惜将自己的作品焚毁。如黄宗羲夫人叶氏宝林,听闻闾内闺秀作诗结社,与男士举杯唱和,遂焚其诗稿;而钟韫和俞绣孙均在去世前焚烧自己的诗文稿,幸分别由查慎行和俞樾抢救整理,结集刊行。
这种驯服的才女意象就集中体现在当时刊印的女性文集常以“焚余”为名,据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就有31种;而强调女性驯服的其他意象还有以“绣闲、绣余、红余”为集名,有156种;以“绿窗”命名的有51种。
这种驯服的才女意象是在强调作为才女的本分是女工、女德,在满足家庭空间的社会与道德规范之余才吟诗填词,强调才女的主要成员资格首先是遵守家庭空间和地域社会秩序的社会成员,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才女的异质性:女才对家庭空间的女德秩序的威胁。(时人批评才女“往往解吟咏,工翰墨,而井臼操作米盐琐屑皆视为末务”。这种驯服的意象与范畴定义可以有效地化解这种对才女不遵守家庭空间秩序的攻击)。而从认知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一般人在头脑中想到“才女”时,首先调用的是有德女子而非有才女子这样的图式。在才女的社会范畴定义中,德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中心性的符号因素。
通过强调德行与才华并重而非仅仅拥有个体性才华的成员资格与群体边界,才女群体使得自身既拥有与家庭空间秩序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又拥有了与社会其他成员和家庭空间秩序之间的同质性,从而使得自己可以安然于家庭空间和地域社会之中,并同时保留了自身的异质性,事实上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隐蔽的,是以表面驯服的身体形象和社会范畴定义展现出来的。
例如,发生在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身上的一件才女逸事。
余辛丑客秦淮,作杂诗二十首,多言旧院时事。内一篇云:“十里清淮水蔚蓝,板桥斜日柳毵毵。栖鸦流水空萧瑟,不见题诗纪阿男”。阿男名暎淮,诗人伯紫之妹也。幼有诗云:“栖鸦流水点秋光”。后适莒州杜氏,以节闻。伯紫与余书云:“公诗即史,乃以青灯白发之嫠妇,与莫愁、桃叶同列,后人其谓之何?”余谢之。后入为仪郎,乃力主覆疏,旌其闾,笑曰:“聊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
纪阿男少时为才女,其个体性的才华甚至得到诗坛领袖王士祯的赞许,但她同时也为节妇,有德行,是遵守家庭空间秩序的社会成员。其兄长认为王士祯的诗句虽然显示了阿男的个体性的才,但却没有展示其驯服的遵守家庭空间秩序的有德女子的形象,致信表示不满。然而细考其兄伯紫的来信,并不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而是觉得王士祯的诗中意象(板桥、秦淮)将才女这样的才德兼备的女子同另一类有才无德的女子(莫愁、桃叶)混淆了,从而危及到了其妹在家庭空间中的形象和地位。纪阿男身为才女,在展现其个体性才华的同时,必须展现出家庭空间中驯服的才女形象和范畴定义,必须和“青楼”这样有才无德的女子范畴边界做出严格的区分,这既是家庭空间对才女的规训技术,也是才女群体面对家庭空间的一种话语策略。
通过这两种话语策略,才女完成了对“才女”这个社会范畴的定义,展示了自身与家庭空间的无害性与同质性,从而使得才女成为普通女性的一个范畴意义的亚群体,在表面上承认了家庭空间对于才女群体规训的有效性,但事实上又保留了自身的异质性。而在才女群体内部,对异质性——个体性才华的强调始终是在德之上的,是群体边界和独特性的体现,是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关键词。
例如女诗人丁白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空间对女性的规训不以为然,“若云无才即德,我窃以为不然。则有巾帼丈夫,香闺学士,冰心玉骨,既解柔嘉,蕙性兰心,更多敏慧”。
才女顾若璞则进一步为才女拥有异质性——个体性才华做辩护,她认为诗文并非女性分外之事。“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左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呈,或亦非分外事也。”通过援引著名的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和左芬,顾若璞将才女试图放置在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地位,强调女才并非在“内”,而是和男子一样,可以在“外”,这就意味着拥有异质性的才女是可以打破家庭空间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秩序的。
个体性的才华成为才女群体事实上的首要标准。在德才不两全的情况下,编选《名媛诗纬》的王端淑称“予品定诸名媛诗文,扬节烈,然后爱惜才华。”除了广收闺秀名媛之诗,其他如“绥狐桑濮者”、“青楼终不自振者”之作,亦皆录之卷内。
然而复杂的是,这种异质性,也有被家庭空间秩序驯服而成为对家庭空间秩序认同的社会成员的可能。只不过,这种社会成员不再是传统的女性,而是同样服从于上下义务性关系的等同于男性士人的女性。如前所述,顾若璞强调女才和男才一样,是可以用于“外”的,这表面上看来,是对男女有别的家庭空间秩序的颠覆,是要打破家庭空间对女性的隔离与固定。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女性就不能凭借诗文之才这样的个体性的才,而是要凭借和男性一样的经史之才,用于“外”的才。顾若璞认为自己有史才。“生具慧性,尤好读史,每夜分执卷,讽咏良苦。曰:‘使我一志读书,即不能补班十志,或可咏雪谢庭。’”
吴绡《啸雪庵自序》也说道:“假使菲薄,生于上叶,传礼经,续汉史,则余病未能;一吟一咏,亦庶几于昔人也。”
然而,拥有经史之才的女性,会被社会空间的这种规训技术通过社会认知的范畴化,从才女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新的女性类型——女经师,从而不再将之视为女性,而视为与男性类似的准男性,用社会空间对男性的社会与道德规范来要求她。
清代的王照园就是这样的被等同于男性士人的才女。王照园,字婉佺,主事郝懿行室。“婉佺书仿欧柳,工古文,得六朝人笔意。尤精汉学,日与懿行考订经史,疏《尔雅》,笺《山海经》,名噪都下。有《列女传补注》八卷,《叙录》一卷,《列女传校正》一卷,《叙赞》一卷,《梦书》一卷。”
王照园的族弟媳秋岩女史,尝有诗奇王婉佺,其小序云:“嫂栖霞族兄懿行室也。兄以著述驰声天下,嫂亦文章博洽,名能与兄偶。学者称为婉佺先生。甲戌冬,嫂自京师以所注《梦书》、《列女传》见寄,赋此志谢”。可见,像王照园这类女经师被视为先生,一种准男性,从而在获得越出男外女内的社会空间界限的同时,也使得自身被社会认知重新范畴化,转换为与才女不同的女性类型而失去异质性。
才女的个体性才华始终被男性和社会视为是文学之才而非经史之才,这样,一方面,才女保留了自身的异质性,但是社会空间通过这种对才的范畴转换,使得才女无法通过这种异质性来真正打破内外的社会空间界限,而只能接受才女的身份,将自己的文学之才用于内:家庭空间之中。这样,才女的异质性对家庭空间秩序的威胁被极大地降低了。
同时家庭空间对女经师的规训会进一步强调,女子的经史之才必须通过“内”为“外”服务而非直接用于外,女经师包括才女必须成为男子的内助,用自己的才华来帮助男性在外获得成功而不是自己出于“外”。这样,拥有异质性的才女对家庭空间秩序不仅不会带来威胁,相反会进一步强化家庭空间内外有别的空间秩序。下面这段发自女性的话很有代表性。
嗟夫!语有云:妇人无才便是德。余窃谓:闺闼中奚必忌言才,第患无识耳。女人之明识,诚可谓知人免难,保家国而助夫者与。
换言之,才女要想真正颠覆家庭空间的内外有别的空间秩序,只有成为具有和男性一样才能的女性。才,在男性那里,是不分的,但在女性这里,被分成了诗文之才和经史之才。拥有后者的才女被视为和男性一样,虽然身体是女性,但却被建构为一种准男性的社会范畴。这样,这类女性对家庭空间的颠覆性通过这种新的范畴“女经师、女史家”和强调以内辅外的空间技术就被消解和驯服了。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妇德的变通性和对妇德的表面驯服两种策略,才女群体部分化解了家庭空间对才女的社会范畴的主要定义: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自身保留了个体性的才,从而保留了异质性;但另一方面,家庭空间通过对才女之才的有效区分,将才女之才视为一种文学之才,是一种主要用于“内”而非“外”的才,通过对“以内辅外”的新家庭空间秩序的确立,从而确保才女无法真正将这种异质性在家庭空间之外展现出来,确保才女群体首先是接受家庭空间秩序规训的社会成员而非拥有异质性的个体,进而确保男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优势地位和内外有别的社会空间秩序,这样,整个江南地域社会赖以平稳运行的基础:家庭空间极其秩序得到了有效维护和再生产。
五、才色俱全:“才女”范畴的性别权力争夺
文章开始提到章学诚对当时才女的批评,认为才女是以色炫人。才女群体的成员资格除了要同时满足家庭空间的秩序要求——德(同质性)和自身的异质性——才,这两个要素以外,才女一般还要具备色。容颜成为才女范畴和群体边界的第三要素。才女何以要有色?这是不是反映了当时才女群体的范畴定义依然是屈服于男性权力的?
表面看来,强调色,是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权力,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这种对才女的色的重视是建立在才女个体性的才的基础上的。换言之,才色不是单纯的容貌,而是建立在个体性才华基础上的女性身体对男性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才色的、个体性的从而是异质性的吸引力,使得才女群体对于地域社会与家庭空间的秩序维护者——男性士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叶绍袁在收录其妻子著名才女沈宜修及三位女儿(纨纨、小纨、小鸾。以叶小鸾才名最著)作品的《午梦堂全集》自序中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叶绍袁将色与才、德并举,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家庭空间中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标准。

《丽姝萃秀图册》之“吴西施”
(图片来源:书格网)
作为才女的丈夫和父亲,叶绍袁自然感受到了才女的魅力。在其妻子沈宜修和女儿叶小鸾、叶纨纨早逝以后,他痛不欲生,追忆不已。“余之伤宛君,非以色也。”“然秀外慧中,盖亦雅人深致矣。”才女即使不是容貌绝美,但才气自然使得其气质和风韵不俗。
而《玉娇梨》这部影响很大的才子佳人小说则借主人公之一的苏友白之口说出了佳人的标准。“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有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有白的佳人。”
刺绣织纺,女红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
守芬含美,贞静自持,行坐不离绣床,遇春曾无怨慕,女德也;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则失风流之韵。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
章学诚更是对才女有色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认为是男性士人吹捧的结果。
今乃累轴连编,所称闺阁之诗,几与男子相埒,甚至比连母女姑妇,缀和娣姒姊妹,殆于家称王、谢、户尽崔、卢。岂壸内文风,自古以来,于今为烈耶?君子可欺以其方,其然,岂其然乎?且其叙述闺流,强半皆称容貌,非夸国色,即诩天人,非赞联珠,即标合璧,遂使观其书者,忘为评诗之话,更成品艳之编,自有诗话以来所未见也。
这种批评恰恰说明了建立在个体性才华基础上的色是当时士人认知才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自然成为才女群体的一种群体边界。
如果说才色德兼具是男性心目中对“女子”的理想标准的话,清初著名文人李渔则把德归属于妻,才色属妾,反映了家庭空间中男性对女性的实际标准。
吾谓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败行;贪淫之妇,何尝历历知书?但须为之夫者,既有怜才之心,兼有驭才之术耳。……(尤展成云:叶天寥以德才色为妇人三不朽。笠翁以德属妻,以才色属妾,更为平论,且可息入宫之妒矣。)使姬妾满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静而彼喧,所答非所问,所应非所求。是何异于入狐狸之穴,舍宣淫而外,一无事事者乎?
李渔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男性对才女的身体欲望,他描述了男性凝视下的才女图像:
妇人读书习字,无论学成之后受益无穷,即其初学之时,先有裨于观者。只须案摊书本,手捏柔毫,坐于绿窗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画图。班姬读史之容,谢庭咏雪之态,不过如是,何必睹其题咏,较其工拙,而后有闺秀同房之乐哉?
可见,男性士人对才女个体性的才的欣赏是与其色(姿态和容颜)混合在一起的。
这种才女身体的吸引力与一般的青楼女子或者妾这样的单纯的身体欲望的吸引力不同,它是建立在其女性才学的基础上的。何以才女会对男性士人产生身体上的吸引力呢?这主要是因为,才女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身的个体性的诗文之才对个体性情感有了比较敏锐的把握,才女多情,这种情是对个体的发现。才女通过“才”成为个体,进而成为身体意义的个体:有情欲和情感表达能力的个体,从而对男性产生了感官和心理上的吸引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都是强调色,但是对于这种个体性的建立在才的基础上的色与单纯的以色事人的色有明显的区别。这就使得“才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与“青楼”产生了有效的区分。
正是这种与才相结合的色构成了才女群体与其他女子的社会范畴意义的群体差异,使得其与社会其他有色女子拥有不一致性。虽然对“色”的凝视与评价表面看来体现了男性对于“才女为何”的性别权力,但是当我们注意到这种色是与才女自身的才华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由内而外的才色而非单纯外表的“色”,男性必须建立起对“才女”范畴自身的中心内容“才”的欣赏,才能拥有欣赏和评价“才女”才色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才色作为才女范畴的内容和群体边界,是才女与士人性别角力的结果。
六、结语
在明清两代,才女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凭借其个体性的诗文之才,呈现出与普通女子的异质性,成为在社会认知中难以确定的陌生人,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士人无法再简单地调用“女子”这样的认知和行为图式来认知才女,而必须发展出新的认知范畴来对这一群体予以定义。那么,才女为何?在这个群体范畴定义过程的背后,体现了才女群体和家庭空间秩序之间的张力和争夺。
通过强调才德兼备,才女群体成功地将自身归类为地域社会和家庭空间所称许的“女子”这一社会范畴中,成为“女子”的一个亚类型,呈现出对家庭空间秩序接受和驯服的意象,从而事实上保留了自身的异质性,并使得社会认知中“才女”的范畴呈现出与普通“女子”的不一致性,而地域社会的秩序生产通过德为才先这样的范畴定义,家庭空间秩序——女德,依然成为“才女”范畴的启动项和代表项,成为才女在认知和行动中无法逾越的范畴边界。在才女与地域社会的范畴定义争夺过程中,“德才兼备”作为“才女”范畴的代表项逐渐被确定下来。才女既是“女子”范畴中的亚类型,是社会秩序的无害者和维护者,同时也可以保留个体性的才华和一定的异质性,与“女子”具有一定的不一致性,家庭空间的规训技术在面对“才女”时,也允许呈现出一定的弹性。
而对才色的范畴定义和群体边界的强调,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男性对才女的凝视权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男性对于建立在个体性才华基础上的才色以及才色的拥有者——才女同其他女性群体之间有了有效的区分。清代以来,才女渐渐独立于“青楼”而成为两个不同的对有才女子的社会认知范畴,同上述的“德”与“才色”的范畴内容强调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范畴定义,将“才女”逐步固定于家庭空间秩序之内,强调其与“青楼”这样有才无德女子的差别,同时又将“才女”与“妇人”有所区别,强调其才能够给予其行动一定的秩序宽容和弹性,这样,“才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被逐渐定义和固定化(即刻板印象化)的过程,也是地域社会与家庭空间秩序再生产的过程,才女的异质性和在认知意义上难以确定的陌生性可能给家庭空间秩序带来的威胁在这种定义过程中逐渐被消解,才女不再是认知意义上难以确定的陌生人,而是可以范畴化、产生认知和行为预期、进行行动预测的社会成员,江南地域社会的稳定运行得到了微观意义的认知和行动图式的保障。
(本文轉自「開放時代」公衆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