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收录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慕容垂歌辞》是引起争议较大的一组。歌辞一共三曲,内容是: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

鼓吹乐俑
三曲歌辞,分别描述了时间上存在连续性的三个场景:(一)被“吴军”围困的“慕容”攀墙眺望;(二)在墙内烧香拜佛,祈求顺利出逃;(三)逃亡出墙。主角“慕容”,按理说就是歌辞标题中的慕容垂。但这正是引起争议之处。按照当时的习惯称呼,“吴军”指东晋军队。而无论是《晋书·慕容垂载记》,还是《十六国春秋》《资治通鉴》及现存的其他相关史料,都找不到慕容垂曾被东晋军队围困并出逃的明确记载。
慕容垂有过三次败于东晋军队的经历。第一次是太和四年(三六九)桓温北伐,在林渚击败过慕容垂、傅末波统领的前燕军。后来慕容垂又在襄邑大败桓温,史称枋头之战,致使东晋此次北伐失利。第二次是在淝水之战前,太元八年(三八三)六月至十月间,时为前秦将领的慕容垂率军援救襄阳,进至沔水,曾被屯戍夏口的桓石民击败于漳口。淝水之战后前秦溃退,只有慕容垂的几万人“独全”,可见漳口之败对其影响不大。第三次是在太元十年(三八五)三四月间,慕容垂率军围攻邺城中的前秦苻丕势力,东晋将领刘牢之率军援救苻丕,慕容垂“逆战”,被击败后,从邺城撤往新城。这次虽然涉及围城,但慕容垂才是围攻的一方,回军迎战时被刘牢之击败。慕容垂退往新城后,很快又在刘牢之追达前弃城北逃。刘牢之率军尾追数百里,最后在五泽桥被设伏的慕容垂军击败。

桓温伐燕示意图(来源:bing.com)
这几次战事,与歌辞描述的情境都不太契合。林渚之战和漳口之战,文献记述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枋头(襄邑)之战,慕容垂是获胜者,更与歌辞情境不符。因此,以往最为主流的意见是太元十年邺城之战,认为歌辞是邺城之中的前秦人所作,以此嘲笑被刘牢之击败的慕容垂(提出此说的是明人胡应麟)。但如前所说,邺城之战慕容垂并非败于“城”中,撤往新城后也未发生围困战,文献记载是很明确的。
于是有学者尝试从“吴军”入手,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认为“吴”并不是指东晋,而是指慕容垂在前燕时期的封爵“吴王”。枋头(襄邑)之战后,“威名益振”的慕容垂深受太后可足浑氏和太傅慕容评猜忌,有人劝他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但他不愿同族相残,选择了从邺城出走。这种解释认为,“吴军”是指当时驻扎在邺城城外的慕容垂所部军队。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说的是慕容垂不愿让城外军队为自己牺牲。
不过,慕容垂从邺城出走,是借口去大陆泽打猎——“请畋于大陆,因微服出邺,将趋龙城”。从“请”字可知,这次出城打猎得到了前燕朝廷的批准,只是朝廷并不知道隐藏在打猎背后的逃亡计划。出城后行至邯郸,不受疼爱的慕容垂次子慕容麟逃回邺城告密,太傅慕容评才获知此事,奏请皇帝派兵追赶。可足浑氏和慕容评已经在密谋诛除慕容垂,假设邺城城外驻扎着直属于慕容垂的“无边岸”大军,同意慕容垂出城打猎,无疑是放虎归山,完全不合常理。

邺城遗址(来源:bing.com)
很显然,将歌辞“强行”推定为慕容垂经历的某次事件,不管如何引申或补救史料的不足,都面临着逻辑上的明显困难。出现了另外一种解释思路——会不会歌辞标题有误,主角并不是慕容垂呢?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多个政权,它们与“吴军”发生的围城战并不多,最惨烈的当属刘裕北伐灭南燕时的广固之战,歌辞主角会不会是指当时的南燕主慕容超?
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有大、小二城。刘裕大军于东晋义熙五年(四〇九)七月攻克广固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小城非常坚固,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围城,直到次年二月才被攻克。围城半年之后,正月朔旦慕容超曾在城墙之上朝会群臣,他的爱姬魏夫人随从登城,“见王师之盛,握超手而相对泣”。《晋书·慕容超载记》中的这个场景记述,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一曲中的“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

广固城遗址
第三曲也跟广固城破时的情形契合。大势已去后,南燕大臣悦寿打开城门接纳东晋军,慕容超选择“与左右数十骑出亡”。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此次出逃是“逾城突围出走”,应当是趁乱用绳索将人、马从城墙上悬下而逃,只是出城之后仍被追获。第三曲重复强调了第一曲的“吴军无边岸”一句,又说“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表现的或许就是慕容逃亡出墙后仍无法突围的绝望心理。
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的,是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从句意来看,显然是说“慕容”攀墙而视,看到墙外的“汉”被东晋军队“枉杀”,因此发出叹息。如何理解这一幕呢?“汉”究竟是些什么人?既然是“枉杀”,当然不是指进攻方“吴军”,而是被围困的“慕容”一方的人。如所周知,十六国北朝时期,“汉”或“汉儿”往往是指华夏之人,以区别于五胡。这方面的用例很多,如《折杨柳歌辞》:“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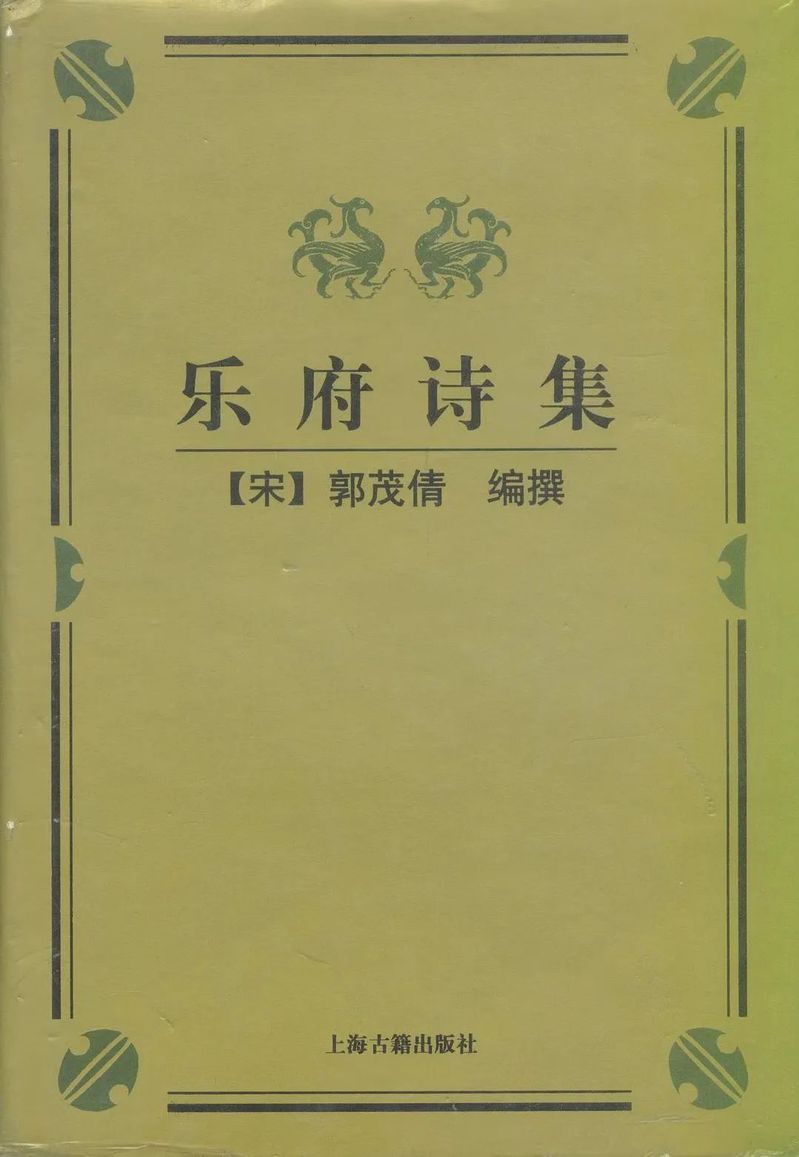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主要辑录汉魏到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其中便包括《折杨柳歌辞》(来源:douban.com)
诸燕政权的统治者是慕容鲜卑,民众绝大多数则是汉人,墙外被“杀”的“汉”,或许可以理解为被东晋军队杀戮的百姓。不过,反复揣摩“我身分自当”一句,感觉更像是指“慕容”一方的军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双方正在墙外进行激战(或刚刚结束不久),死伤惨烈,墙上的观看者不由生出内疚之叹。
假设“慕容”是指慕容超,这个场景显然就不是上面提到的正月朔旦城上朝会,此时并未有战事发生。广固围城期间,有记载的南燕唯一一次出城作战,是在这次朝会之后,由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掘地道出城作战,最终失利。这种作战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像是自杀式的突击,一旦失利,很难再顺利退回城中。两位将领贺赖卢、公孙五楼,此后未见记载,很有可能是死于这次突击。
两位将领中,贺赖卢是从拓跋魏投奔慕容德的,从姓氏看出自匈奴。公孙五楼籍贯不详,但慕容超祖母(慕容德母亲)姓公孙,公孙五楼应当来自同一家族,推测是辽东或辽西大族公孙氏。慕容超自幼与祖母、母亲(段氏)生活在关陇地区,颠沛流离,慕容德去世前不久才到南燕,跟南燕统治层关系比较陌生,因此即位时权力很不稳固。这使得他对于祖母和母亲的家族非常倚重,特别是公孙五楼,最受荣宠信任,以至于当时曾有一种说法:“欲得侯,事五楼。”可以想象,若是公孙五楼出城突击作战被杀,对于慕容超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打击。这就让人怀疑:歌辞中被“枉杀”的“墙外汉”,除了有可能是指挖掘地道出城作战的南燕军人(或许主要是汉人步兵)外,会不会也跟公孙五楼有关呢?果真如此的话,这句歌辞就具有了不一样的凭吊和感伤情绪。这当然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但如果歌辞确实与慕容超有关,总不免让人对此浮想联翩。

南燕,慕容德所建,统治范围包括山东及江苏一部分(来源:bing.com)
出城作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围城太久,等待后秦援军也已无望,只能冒险一试。突击失败,东晋军队又塞五龙口,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彻底难以支撑。此时慕容超曾“辇而升城”。第一曲中的“攀墙视”,倒是很契合他此时身体虚弱、扶墙勉强而视的场景。而城下应当还残留着贺赖卢、公孙五楼突击失败的残局。
慕容超没有考虑过投降,曾杀死或囚禁过一些劝降的大臣。“辇而升城”时,感叹而回答劝降的大臣悦寿说:“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不能衔璧求生。”第二曲中“愁愤愤”的“烧香作佛会”,祈祷的是顺利出逃,也契合他此时的心境。被俘后,刘裕责备他为何不降,慕容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刘裕恼怒于城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后来听取韩范进谏,放弃屠城,“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慕容超的坚持不降、被俘后的坦然,与围城中的苦难、城破后的屠杀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

刘裕,南朝刘宋开国君主(来源:bing.com)
如不考虑标题,只看歌辞内容的话,三个场景与广固围城确实若合符节。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表明东晋军队围城的目标是“慕容”,而不是一般性的军事攻防。广固围城是要灭南燕,身为一国之主而又不肯投降的慕容超,发出这种感叹,较之慕容垂败于东晋军队的几次战役,语境上也更为契合。但通过改字而重新理解史料,是实证史学的大忌。《慕容垂歌辞》究竟有没有题目讹误的可能呢?
包括《慕容垂歌辞》在内的“梁鼓角横吹曲”,最早见于陈代僧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至迟梁代已经使用这一标题。更早的来历则不清楚。“梁鼓角横吹曲”总共六十六曲,分为三组。这些歌辞来源复杂,既包括“燕魏之际鲜卑歌”,也有南方歌谣,还有汉代流传下来的横吹曲辞和民歌。其中有一些明显与前秦、后秦和慕容诸燕有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对横吹曲辞有一个总的解题,就说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但稍读歌辞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六十六曲歌辞之中,有些是青年男女的恋情,有些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感悟,有些是社会底层的奋斗,而直接描述“战阵时之事”的歌辞,实际上就只有第一组中的《慕容垂歌辞》和第三组中的《隔谷歌》。此外还有涉及军人的《企喻歌辞》。
《隔谷歌》讲述的也是一个围城场景: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骑马吹角俑
歌辞的主角是一位守城军人,弹尽粮绝之际,向城外可能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弟弟发出求救的呼喊。可惜的是,具体时间、地点和事件均不详。《企喻歌辞》共有四曲,第二曲(“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第三曲(“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从内容来看描述的应当是军人或军队生活,但并不直接涉及“战事”。值得一提的是,《企喻歌辞》的第四曲(“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古今乐录》明确提到了作者,是前秦苻坚之弟、死于淝水之战的苻融。该曲表现的是军人战争死亡的悲惨,与《企喻》前三曲表达的昂扬情绪完全不同。可以推测,前三曲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记述的是乱世之中“男儿”(军人)建功立业的追求,是一种“男儿”视角的表达。苻融补作的第四曲,则是一种旁观者视角,对乱世男儿的生命陨落,心生悲悯。
歌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五胡政权统治下的北方,传入江南的过程可能比较复杂。鼓角横吹曲原本是军队之中演奏的乐曲,乐器之中有鼓角,“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东晋中后期的几次北伐胜利,尤其是淝水之战和刘裕灭南燕、后秦之役,应当是比较重要的南传契机。东晋的北伐进军,不仅仅是军事行动,可以想见也会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歌谣也会在其中。

淝水之战概念图(来源:bing.com)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产生契机来看,《慕容垂歌辞》在“梁鼓角横吹曲”中都显得非常特别。其他歌辞在东晋北伐之前应当已经存在于北方,有些甚至可能是传唱已久的“民歌”(或部分补作)。描述东晋军队围攻事件的《慕容垂歌辞》,则是北伐战事的见证,属于“实时性”作品。这就让人心生疑问:歌辞的作者会是谁呢?
这个问题当然更加难以落实。之所以对此抱有疑问,是由于歌辞明显的亲历见证者色彩。三曲歌辞对应着三个连续的场景,就像三幕舞台剧,描述了被围困的“慕容”从叹息到绝望,从祈祷到出逃的过程。前两个场景发生在“墙”内,“吴军”破城之前自然是看不到的。第三个场景则是出逃后被追获之前。从常理来说,这几个场景更应当是战事结束之后,由胜利者即东晋一方,通过询问、采访城中俘虏,而获得的“慕容”失败前后的信息,由此创制为军乐歌辞,彰显军事胜利。果真如此的话,歌辞就具有了复合性的意涵,一方面是胜利者的声音纪功碑,一方面也是围城中人的记忆。
这也让人再次想到广固城破时的情形。刘裕的屠杀行为,与歌辞表达的情绪,倒是共同彰显着胜利者的姿态。从韩范的谏言可知,围城中有不少“衣冠旧族”即汉人士族,韩范想尽力保护的主要是这批人。其中很多都是随从慕容德南迁的河北大族,南燕灭亡后,他们有些离开了青齐,但大多数人仍旧生活于当地,延续为青齐地区支配性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所谓的“青齐土民”。由于多多少少都有家族中人经历过广固围城之役,像正月朔旦城上朝会、挖掘地道出城作战、慕容超“逾城”出逃这些重要事件,必然会作为围城掌故,成为他们家族记忆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南燕史事,最早正是经由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之手,书写和记录下来的。

邓县画像砖上的鼓角横吹俑
广固城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南燕有一批旧太常乐人,慕容超即位后,由于母亲和妻子仍在长安,后秦姚兴以此为借口,要求他称藩,并遣送这批乐人或“吴口千人”到长安。南燕左仆射段晖认为,这些太常乐人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不能遣送——“太常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略吴口与之”。但迫于压力,慕容超最终还是送了一百二十个乐人给姚兴。此事甚至被看作后秦统治兴盛的一个象征:“皇秦道胜,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慕容超被迫送出一部分乐人后,正旦朝会“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发兵抄掠刘宋边境,“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这件事成为刘裕北伐灭南燕的直接口实。留在广固的太常乐人们,在经历围城事件之后,应当会被作为战利品带回建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创作和传承乐歌,是乐人的本行。据《古今乐录》记载,《隔谷歌》“前云无辞,乐工有辞如此”,《高阳乐人歌》是“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旧唐书·音乐志二》叙述北狄乐源流时,提到一位歌工长孙元忠,家族传习“北歌”数代。《慕容垂歌辞》的制作,会不会与军中乐人有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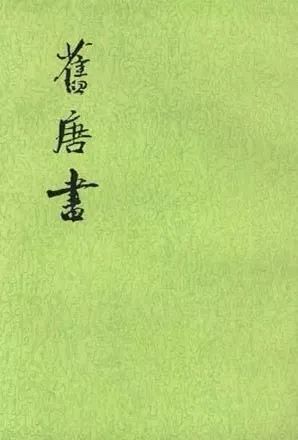
《旧唐书》(来源:douban.com)
乐歌包含歌辞和曲调两部分。作为描述城破胜利的军乐曲,歌辞有可能是乐人创作,也有可能是文士写作或改定。但不管歌辞作者是谁,最早都应当是由军中乐人来演奏歌唱的。东晋北伐军中有随军乐人,围城之中也会有乐人,他们都有可能是《慕容垂歌辞》最早的相关者。至于歌辞最初的标题,并不清楚如何命名,也不排除是像有些乐府歌辞那样,采用首句中的某个词语,比如指向性模糊的“慕容”,作为标题。从歌辞产生,到成为“梁鼓角横吹曲”,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原来的歌辞标题只是指向性模糊的“慕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歌辞产生的语境成为历史,就有可能出现传承错误,将主角从指向性模糊的“慕容”,讹指为慕容氏的某位“名人”。而慕容垂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很强标靶意义的“名人”。《旧唐书·音乐志二》提到的歌工长孙元忠家族,传承“北歌”时就存在失真现象:“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也已经感觉到,将歌辞场景推定为广固围城,不仅细节契合,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维度。但尽管如此,歌辞标题显示的主角毕竟是慕容垂,没有丝毫的乐府文献证据可以推翻这一点。歌辞背后的真实历史究竟是什么,仍然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不过,历史学研究的目标,原本也不仅仅是探求真相,“不是使隐者显或者浊者清,而是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这既是一种永恒的轮回,也是一种同时深具艺术与伦理意涵的(自我)解放”。这是叶启政在《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对于社会学诠释目标的一个讨论。历史学虽然更加侧重于事件和时间分析,与侧重结构和机制分析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慕容垂歌辞》的解释上,研究者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文献可能性,但都难以完全“砸实”,找出历史的“真相”。慕容垂的生平经历与之难以吻合,更为契合情境的慕容超和广固围城事件,却与标题不符。从文献考证的游戏规则来说,只能到此止步——指出歌谣与历史的矛盾之处,并谨慎地推测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随着各种可能性的提出,不管是将其比定为邺城之战,还是对于“吴”字的新解,抑或将主角改字理解为慕容超,相应的想象历史、感受历史的场景,显然也被研究者建构出来了。这些建构当然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可以确信的是,正是由于这三曲存在争议的歌辞及其可能性探讨,使得一些原本在文献记录中并不那么受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具有了某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叶启政著《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来源:douban.com)
这也许是值得历史学者思考的一个现象。面对学术问题时,尽可能地搜罗各种证据,构建相对合理的逻辑链条,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而在文献考证的止步之处,进一步驰骋想象的翅膀,分析多种多样的历史可能性——“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同样也是这门学问令人沉迷的魅力所在。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现代历史学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肯定。当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再过分执着时,历史想象与场景构建的价值就愈加重要起来。就像《慕容垂歌辞》,那种围困情境中的彷徨、绝望、祈祷和叹息,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仍然感同身受。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讀書》2023年第3期。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