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酸往事
我是1949年12月22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出生在福建前线的闽南农村。由于土地少而人口多,当时的农村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而我家则因小孩多、劳力少,可以说几乎是全村最为贫穷的,因此,我的童年经常要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尽管如此,大字不识的父母依然送我去读书(其他姐妹均未读书),以求今后能有“出息”。他们拼命劳作、省吃俭用,母亲甚至一度去当奶妈,以贴补家用。小学毕业后,我顺利考上了重点中学(南星中学)。1963 年9月1日,满怀喜悦之情的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到,可当获知要交23元学费和住宿费(一学期)时,我们顿感晴天霹雳,因为父亲的口袋中只有好不容易筹借到的5元钱, 实在交付不起学校所需的费用。无奈之下,我只好回家种地。过了两个多月后, 我的大盈小学班主任吕良基老师得知我辍学在家务农时,很是为我可惜,于是借钱给我家(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大家生活都很困难),使我得以入学读书。每思及此,不禁潸潸,吕师恩情,永铭五内矣!
谁知初中刚毕业,“文革”就爆发了,全社会都在停学闹革命,我只得回乡重新拿起锄头去修理“地球”了。不过,作为本地读了点书又有点才气的小青年, 不久我便被抽调到大队部搞宣传工作。尽管后来我又在南侨中学读高中,但在“政治统帅一切”的当时,能学到多少知识呢?直到1970年11月,适逢南安水头农械厂来招工,因我曾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吹笛子,有些特长,机缘巧合之下被选中,进入到农械厂铸造车间当学徒,每月工资18元,从那以后生活才稍有好转。可是我的父母仍因生病,无钱医治,先后离我而去,思之泪下。
迨至1974 年9月,我有幸进入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从此踏上了改变命运的考古之路。当时的我很穷,甚至连蚊帐都没有,还是老师们特地为我向学校申请借到了一顶。读书期间,我全靠每月13 元的助学金来维持生计,生活之难可想而知。1977 年9月3日,毕业后的我来到了浙江省博物馆工作,随身携带的行李也只有一床 10 斤的棉被和两件衣服而已。报到没几天,我就立即奔赴河姆渡遗址,开始从事繁重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此后,我经常出差在外, 足迹几乎遍及全省各地,却从不感到辛苦。后来,考古部自省博物馆析出,创建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也随之迁入。1986 年,我有幸调入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和研究条件大为改善,成果也与日俱增,直到2013年7月退休。但我依然退而不休,始终坚持对史学的探索与研究,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我之所以讲这些经历,无非是想告知大家:
我本是农村出身的穷苦孩子, 天资并不聪颖,只是深知昔日生活的艰难,故而从小就练就了吃苦耐劳的坚强毅力,知道今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确实来之不易,理应更加珍惜。同时,由于过去读书不多,知识有限,更应加倍努力地读书,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 之意。所以,40 多年来,我仍保持着朴素、正直、勤劳、吃苦的本色,生活十分简朴,从不贪图物质享受。现今我每天都要看专业书、做卡片,认真搜集相关史料与考古信息,解读、剖析有关问题,几乎每天都到凌晨 1 点多方上床入睡。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成绩、并被评为二级研究员的话,那就是我数十年如一日, 透支生命、用功读书、严谨治学的缘故。
勤奋治学
在农村“苦水”中长大的我,深知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唯有努力工作、勤奋读书,学好专业知识才会有出路。早在厦大期间,我深知此前自己读书太少, 更无条件买书,因此格外珍惜学校中难得的机会和条件,一有时间就会到图书馆看书、做卡片、记笔记,如饥似渴地汲取史学知识,并力求学以致用,经常利用假期徒步进行考古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家乡附近发现了一批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和玉器,这在当时可说是福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查阅了不少资料,撰写了自己的处女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一文,发表在权威专业刊物《考古》(1977 年第 3 期)上,一时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我也由此对吴越文化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正是我在毕业后选择来浙江工作的原因。
“秋风烈,盈水咽,泪沁心兮故乡诀 ;辞家夺魁酬吾志,愿将热血洒五岳”。
这是我在1977年9月3日自闽来浙的火车上写的一首小诗,正是当时自己心情的写照。刚到杭州时,无论是气候还是生活都有些不习惯,尤其是孤身一人远走他乡,既没有老师、同学或亲人在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说“举目无亲”,凡事都得靠自己。加上我为人正直、不善言辞,往往容易碰壁。经过了几番坎坷后,我逐渐对自己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努力工作、勤奋治学,在学术道路上求生存与发展。当时在省博物馆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上班除了学习政治、召开会议或讨论工作之外,便是谈政治、看报纸、聊新闻或打电话、谈空天,加上人来客往又较多,整天闹哄哄的。我不愿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闲谈之中,为了排除干扰,经常会用棉花团塞住两耳,以集中更多的精力去看专业书。即使后来结婚有了小孩,家人晚上要看电视,我依旧还是耳塞棉花团看书写字。所以,在我的档案中往往会有“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评语。40多年来,我几乎从不看报纸、看小说,也不看电影、电视,更不会去打牌、喝酒或者逛街、游公园,甚至后来生活条件改善,我依旧不讲究吃穿, 继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这里可以讲一个小笑话:
我记得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当时我在省政府大院内的省社科院工作,平时不用天天上班。有一天我去单位时,突然被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下,可能是我穿衣服不够有品位,抑或是自行车较旧,那位武警同志检查完我的工作证后,依然怀疑是假的(可能证件照片太旧),误以为我是上访的,说要打电话再次核实。至今这件小事仍被大家传为笑谈。
我做学问是很用功的,治学也很严谨,从不走捷径,不写投机取巧的聪明文章,或作抱佛脚的应景应时之文,可以说是“苦行僧式”的学者。
举个例子 :
我自1992 年开始着手撰写《良渚文化研究》一书,前后长达五六年。当时为了写好此书,我让老婆和女儿租房住到了她单位附近,自己则在朝晖新村关起门来“造书”,不分昼夜(每天只烧一次饭)。1993 年,日本天皇的老师,京都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林巳奈夫赴江西开会前途经杭州,下榻在望湖宾馆后给我打了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写书时有一习惯,每天“闭门造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为了方便查阅资料,会将笔记、卡片、期刊、书籍、草稿以及资料摊开在家里的书架、床上、床下、桌上、桌下以及房间和小客厅的地面等处。我家与望湖宾馆仅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的突然到访让我措手不及,完全来不及收拾,我只得硬着头皮与他匆匆见了面。他惊叹于我做学问时的“疯狂”和专注, 并提出可以为我的《良渚文化研究》这本书写“序”。序言中记录了当时他在我家中所看到的一切,写道 :“这本书就是来自那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的一部分,我想它肯定将不负众望。”其实,先前出版的《河姆渡文化初探》,也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另一件事情也让我记忆犹新 :
大约是1994 年的大年初一,省社科院副书记杨金荣突然来访,向单位中各家拜年。当杨书记一进我家门,看到我独自一人在家,依旧是随处可见摊开的书籍、期刊、资料,他惊叹不已,说 :“我就是没有照相机,不然真应该将现场拍下来,让大家知道林华东在新春佳节,依然在如此用功地做学问,实在太苦了!”
治学方法
我原是考古出身,主要做先秦史领域中的吴越文化和史前研究工作。在厦大恩师庄为玑、蒋炳钊、吕荣芳、陈国强、李家添等教授的培养指导下,我很早就明白治学方法十分重要,尤其是做史前史和先秦史,既要懂得考古文物蕴含的历史内涵,又要能与古代文献相结合来进行解读研究,方可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这也正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双重证法”,效果确实很好,我对此体会尤深。
我认为,假如纯粹以古代历史文献来研究先秦史,高校的教授或相关的历史研究机构,早就对古代文献记载十分精通,如数家珍。而如果从考古文物资料, 瓶瓶罐罐的器物排队、分型定式着手,又已有众多的考古前辈做出了很好的探索。不过,我发现从事古文献考证的专家往往对考古实物重视不够,或缺乏深入的理解,而从事考古工作的前辈,则容易忽视古代文献中的历史线索及地理变迁, 也就是说两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研究吴越文化十分注重古代文献和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从而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现举两个事例 :
其一,萧山湘湖越王城的发现与考证。
1979 年,我在省博工作期间,领导派我去今日钱塘新区蜀南街道的蜀山遗址(原属萧山)搞调查。当时萧山文化馆的蒋毅说 :
“县志上曾记载湘湖边有个叫‘越王城’的地名,不知何故?就是没有城垣。”
因为我是研究越国史的,听后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两人立即骑着自行车前往,并徒步爬山而上进行实地考察。我认为既然古代地名叫越王城,必然不会空穴来风,肯定有它的历史传承等信息。这里处在城山之上,山脊蜿蜒逶迤绵亘于山岗之巅,城中四周(除马门外)高起,宛如小盆地,应该是有城垣的,只是山脊与城垣难以辨别区分之故。回家后我立刻查阅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并先后20多次独自上山调研考察,终于发现了四周的城墙和越国的印纹陶、原始青瓷片等实物证据,由此再联系到古代钱塘江河口的历史变迁,从而肯定了范蠡大船军所筑的固陵城就是这座越王城,这一论断推翻了 2000 多年来历代学者所说的“固陵城是在西兴”的传统误解。此后,越王城又进行了考古试掘和专家论证,终于确认就是越国固陵城所在。越王城由此从历史迷雾中崛起,一跃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开辟为湘湖历史景区,供人们旅游参观。
其二,秦汉钱唐县地望新考。
众所周知,杭州的前身源自秦汉之时的钱唐县, 那么,其时钱唐县(指县治或县城)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史载“灵隐山下”,但学界对此的定位却是众说纷纭、观点迥异。古人曾说在“钱湖门外”,也有认定是在“栗山”(今灵隐法云弄石人岭)。当今有些学者认为应在浙大玉泉校区至植物园,也有的主张在转塘至中村一带,还有人认为应在半山崇贤至石塘附近。
我多年来就很关注此事,查阅了不少古代文献记载,并经常实地调研考察, 特别是十分注重杭州城区和西湖疏浚时出土的历史文物,以及历年发现的墓葬分布和地理历史变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剖析,结合古代文物与相关墓葬的发现,来全面揭示论证钱唐县治所在。同时还认为钱唐县志的探索当不可忽视研究西湖的形成,以及城区古代诸座小山的分布及其沧桑之变。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因东汉华信所筑的“防海大塘”,西湖才与海隔绝,今日的杭州城区才开始成陆。其实,这种说法是有误的。我早就指出华信时的“防海大塘”,应在中山路的羊坝头至众安桥、仙人山(今仙人苑附近)一带,说明“华信所筑‘防海大塘’内侧早已成陆,并且已有较大的聚落存在。不然,何必兴师动众兴筑此‘防海大塘’呢?”再者,延安路灯芯巷口唐代龙兴寺石经幢基座已在今地平面以下2米,2008 年9月发掘的古钱塘门遗址也“离湖滨地面近两米深处”,而今日西湖平均水深只有2.27 米,足以说明秦汉之时的古代西湖“面积并不大,水位要比今日低很多(至少2米)”。正因为湖小水浅,无足轻重,故而不见文献记载乃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在 1984 年杭州环城西路扩建中,在凤起路口原都锦生织锦厂至杭州十四中学路段曾发现五口汉代陶井圈和板瓦、筒瓦等遗物,在遂安路口至教场路口地段有汉代水井、瓦片及陶片等发现,望湖宾馆一带也有汉代陶片和两晋时的青瓷片出土。前几年杭州地铁1号线施工,在凤起路站地下还发现了汉代钱币和陶范。再联系到锦带桥至学士路一带水域中,20世纪50年代西湖疏浚时曾有商周至汉晋文物出土,因此,我主张秦汉时的钱唐县应在宝石山东部,中心地带在少年宫、霍山、弥陀山、省府大院、虎林山(原都锦生织锦厂)、武林路昌化新村至望湖宾馆及古钱塘门一带范围之内,这是古文献结合考古发现而得出的结论。
研究史前史和先秦史,除了应将古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之外,我认为还应重视人类学资料。当某些考古史迹现象难以解答时,参考相关的人类学调查资料,或许有望释疑。拙著《河姆渡文化初探》和《良渚文化研究》的撰写, 正是基于这种治学方法。曾有专家评论说“将枯燥乏味的考古论著,写得有血有肉、生气盎然,此则‘礼失,求诸野’的一种范例”。1991 年8月,我应邀到日本,作题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的演讲,后来又到佐贺县参观考察弥生时代的大型聚落,即吉野里遗址,看到遗址有座瓮棺葬中,死者自脖子以下的人骨架保存完好,却唯独没有头骨。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是死者生前被斩首示众之故,我则由此联想到古代人类学中的猎头习俗。因为该瓮棺葬是在平民墓地,瓮棺中也无任何随葬品,而弥生文化正处在日本稻作农业发展阶段,显然是当时流行猎头习俗的案例。回国后我便撰写了《吉野里遗址所见的猎头习俗》一文,1993年1月发表在东京《东亚古代文化》第76号上。文章率先提出了弥生时代有猎头习俗,引起了日本史学界的重视和民族学权威专家的支持。我也因此获得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的海外研究基金,又于1994年9月至10月再次应邀出访,同日本学术界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做了演讲。
笔耕不辍
人生苦短,唯将学术作为生命之本,人生才会发光。40 多年来,为人正直、不谙世故、生活简朴的我,始终惜时如金、默守书案。自度从不曲学阿世,蘸着心血,缜密思维,笔耕不辍,终日埋头于故纸堆中,与古今学者共斟酌,权将此心留汗青,以酬吾志。
先后已出版学术专著6部、文史读物6部(少数为合作)、主编论文集5部、文物图书6 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180多篇、文史类文章150多篇,以及120多篇科普或收藏类文章等,也先后应邀前往日本、韩国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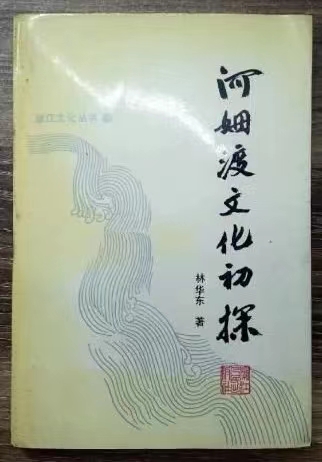
其中专著《河姆渡文化初探》,28 万字,1992年4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奈夫,江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农业考古》主编陈文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等著名专家为此书作“序”,是第一本全面探索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学专著。曾获浙江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浙江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中国社科院夏鼐考古学成果优秀奖(至今国内未见个人专著获过此奖)。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曾称 :“此书对以后研究中国史前史或华南史前文化的学者及学生来说是本必读的书。”《中国史研究》《中国文物报》《东南文化》《南方文物》《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都发表了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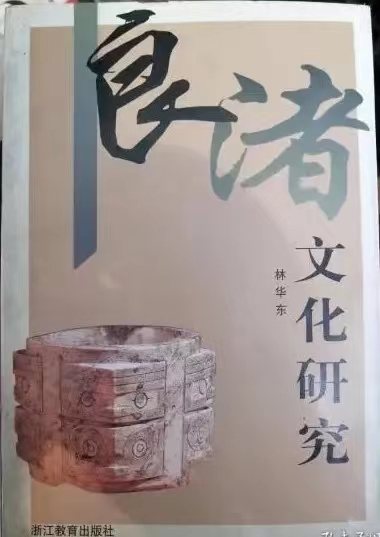
《良渚文化研究》专著,45万字,1998年11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奈夫,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安志敏等著名学者为本书作“序”。这是第一本(也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研究良渚文化的考古学专著。曾获浙江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浙江省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史研究》《中国文物报》《南方文物》《文汇报》《浙江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书评。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曾称 :
“此书写得非常成功,内容丰富,论断明确,将是良渚文化的有力参考书,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著名农史学家、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的游修龄教授,当时曾来信评论说 :
“此书对于各家不同的学术讨论观点,不偏不倚地作了介绍,最后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一个谨严学者治学的可贵品质。对比当前学术界一种浮躁的风气,实在是一个无声而有力度的榜样。”
良渚文化发现已60年,遗址、遗物众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安心下来,从事全面的梳理、研究,作出集大成的贡献,大作是第一部这样的书, 是良渚遗址发现 60 年来的里程碑,特此申贺”。台湾故宫博物院、著名学者邓菽苹研究员也来信说 :“很佩服您的功力,各种资料收集翔实,见解高超。也很会绘制线图。”

《浙江通史·史前卷》,43 万字,2005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全面探讨研究了浙江从旧石器时代到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好川文化,阐明了史前先民的区域特色及精神文化世界。全套《浙江通史》曾荣获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第十五届浙江树人出版奖特等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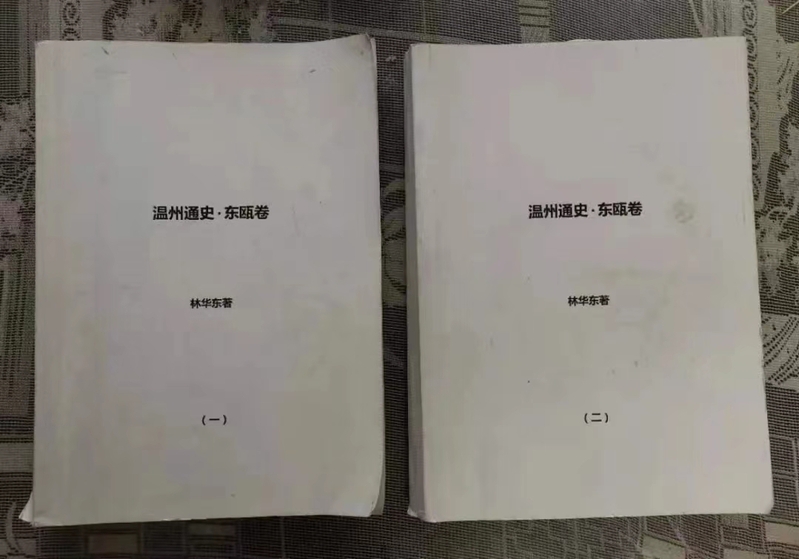
《温州通史·东瓯卷》是温州市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我主要负责第一本即“东瓯卷”的撰写,约60万字,已定稿,将由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研究范围涉及温州从史前至汉代的历史,重点探索东瓯国的建立、兴盛及至消亡的历程。率先提出秦汉时东瓯国都应在瓯江南岸的鹿城区瓯浦垟至华盖山、海坛山、松台山一带,既不可能在瓯北,更不可能在台州市的温岭大溪。

《秦汉以前古杭州》,18.6 万字,2011年9月由杭州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多年关注杭州“童年”,即钱唐县与古西湖形成的心得,力求从考古文物发现提供的线索出发,结合古代文献和历史地理变迁等角度来全面分析阐释,发他人所未发,对不少传统观念多有所突破,反响不错。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此书的出版资助。而今一晃已经10年了,我又积累下不少新的考古文物线索和新的史料、观点,很希望有可能得到进一步补充、完善,将此书修订再版,为杭州文史研究尽绵薄之力。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林華東口述,周佳整理。原載《杭州文史》第二十一輯,另載“杭州文史”公眾號2020年12月9日。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