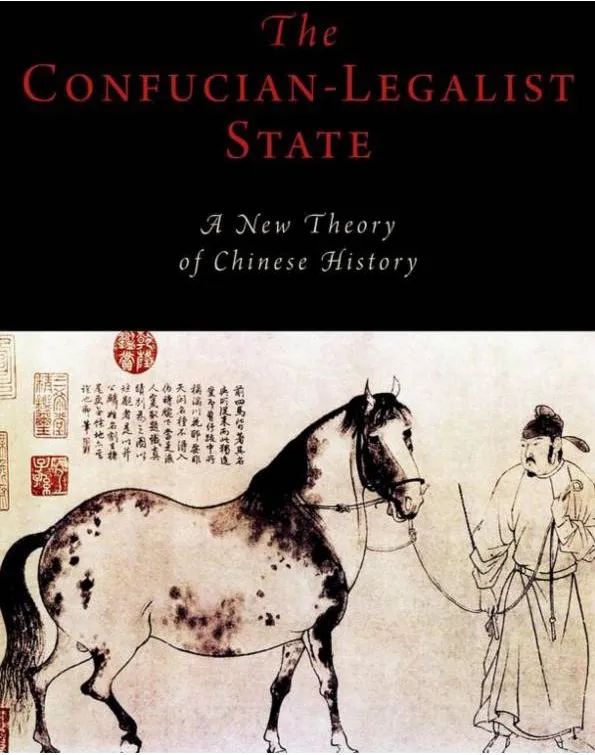
编者按: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
非常荣幸能被邀请为这部精彩的著作写一份简短的书评。第一次与该书作者见面时,他还是就读于麦吉尔大学的学生,自那时起,我就对他很是钦佩,而今天他对中华文明特质的阐释工作圆满完成,我为他感到高兴。我在本文中的评论只不过是把作者书中所讲的内容又强调了一遍,原因极为简单,因为我自己的观点(Hall,1985)与作者的非常一致。等一下再来说我的评论,其中有一部分,我将引入一个比较的维度来为作者的主要观点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但在此之前,有必要谈一下我对该书整体上的两点粗浅感受。首先,作者总体的理论立场在我看来既新颖而又令人兴奋。鼎新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张,即人类社会生活包含着权力、财富与信仰这三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他又采纳了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理论,将军事因素引入到这一模型中,但他为这个模型加上了一道更具刚性的边界(a harder edge)。他相当合乎情理地将互动以达尔文式的术语表述为无止境的持续斗争。对所有这四种因素的性质,他都做了有趣的论述,其中,他对宗教和国家相联系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不过,有别于韦伯和曼,他坚持主张这些社会权力资源之间通常存在着等级关系:在他看来,政治权力主导一切,甚至比军事实力更为重要。这个观点发人深省,且是从实证研究中得出,但我不太确定是否能完全接受作者的这种看法。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得以长期保持其凝聚力当然依靠的是意识形态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另一方面,不单如作者所言经济和军事力量会不断发展,宗教本身也在发展——至少盖尔纳(Gellner,1988)就曾对此做过有趣的论述。而且,理论模型的益处仅仅在于它能打磨提炼我们的思想,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与理论不相符合的现象,我最近的研究就让自己开始稍稍跨出这种韦伯式的理论框架来进行思考。比如,历史记忆就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我近来有一种感觉,欧洲在可怕的20世纪所经历的许多历史教训正在被人们遗忘。西方学者常常强调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自由国家彼此互不侵犯的主张,可他们却忘了,康德还认为其他地方的战争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这样,那些自由国家才能一直认识到和平是对它们有益处的。至于我对该书整体上的第二点粗浅感受,简单来讲,就是它为历史社会学中非常多的问题都分别做出了高水平的社会学分析。例如,作者对魏特夫“水利社会”理论(hydraulic society thesis)的质疑(Zhao,2015:204-207)就无疑是正确的,再如,他在第11章中有关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本身就足以令人拍案称绝。这一点简单总结起来,就是作者的学术见解非常深刻。此外,19世纪英国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在东英格兰的大沼泽地(the Fens of Eastern England)漫步丰富了他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作传的材料与灵感。该书也是一样。鼎新探访了他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地区,并在相关章节中添加了不少考古出土的材料以佐证其观点——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些是新近才出土的,另一些则是地方博物馆收藏的文物。
这部著作的主要观点带给我很多喜悦,其中之一,便是该书认识到那种渐进式发展,即那种时进时退、震荡起伏中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模式。此处,我不再详述这一转变过程,仅就这套模型中的两个要素展开讨论。在该书中,作者搜集了早期中国历史上三段被明确划分的历史时期中有关战争的后勤补给能力、参战人数与伤亡人数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极高,这使作者能将这段血腥残酷的历史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这些战争愈演愈烈,直至彻底走向了全面战争。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周详细致,叙述脉络惊人地清晰明了,就算是那些不熟悉早期中国历史的人也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些战争与欧洲战争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有着明确的最终结果。国家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直到一个国家征服其所有对手。很大程度上,这是推行法家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后果。这也许可被称作是霍布斯主义(Hobbesianism)的更纯粹的形式。因为,实际上霍布斯论述了国家权力绝对化所需的全部条件,但缺乏一套此后仍可让市民社会的组织及其能力蓬勃发展的办法。相比之下,权力在中华文明中注定是绝对的权力。这里必须要展开谈一下具体细节。一方面,秦朝出现的第一次统一非常短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彻底走上大一统的道路。历史证明,后来的西汉王朝实现了更为有效的国家统治,因为他们与残存的贵族势力达成了妥协。但根据这个系统的逻辑,这种造成分裂的封建因素迟早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最终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国家模式。到这一步,模型中的第二个要素才凸显出来。没有哪一个前工业化国家有能力控制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换句话说,国家或许能打败它的对手,但单靠它自身,是无法带来社会稳定的。于是,儒家学说被添加到法家学说中,两者之间的充分融合直到宋代才最终结晶(crystallizing)。这里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儒家学说为社会提供了日常的合法秩序。但这也是分阶段的,它是从精英群体逐渐深入到某些社会关系中,最后扩散到整个社会层面。儒家伦理本身让我这个英国人想起了那些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在那里,责任,永远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理性,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被认作是最为重要的品性。其次,儒家学说最终赋予了国家一种特殊的形式。虽然皇帝偶尔会突然做出一些“圣意独裁”之举,但在更深层次上,他们仍受到官僚集团的严格约束。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模型的解释效力,我们可以拿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文明来做比较。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内亚(Inner Asia)的游牧民族与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该书中的几个精彩段落(Zhao,2015:299)就指出,内亚游牧民族之所以最终被中国社会同化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没有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制度。伊斯兰武士则与之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将武力与信仰融为一炉,也就是说,一种世界性宗教与军事权力媾和在一起(Cook & Crone,1977),这因此影响了国家权力的性质。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是否能遵循圣规圣训,某种意义上,这很容易使统治者招致不敬神明的指责。加之,正如14世纪的伟大学者与社会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所强调的那样,地中海盆地的生态环境导致这里一直有游牧民族存在,这也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性。对此,有人或许可以强调说,这一地区部落之间的血缘纽带不断威胁着国家权力。中国则与此有着巨大的差异:正如鼎新在书中揭示的那样,这个文明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建立在血缘关系对国家支持的基础上,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血缘关系对地方社会秩序的维系来实现的。这里可以再多引申一点,鼎新的言外之意是西方国家的权力相对弱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在西方,意识形态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确不像在中国那样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意识形态选项。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对于西方世界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他却忘了,西方国家也会以有别于伊斯兰国家的方式强化它们的权力。由于贪图大家族的财产,天主教教会破坏了家族血亲的势力,同时也就削弱了世俗社会对它的反抗力量(Goody,1983)。
鼎新关于中国与西方战争差异的论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首先,他强调了地理的作用。中国的战争发生在温带地区,因而战争持续不断,直至出现定于一尊的最终结果。在欧洲,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法国和德国等中等力量的国家必须同时处理来自海洋和陆地上的战事,可能还要面对俄罗斯酷寒的冬天。因而,称霸欧洲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时,俄国已遭受重创,而且若不是德国做出了发动潜艇战的重大决定,让美国也被卷入了进来,它本有可能统治整个欧洲大陆。但除此以外,同样有趣的是,他还指出中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战争行为的共同准则,这就让优先建立帝国统治成了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最终结果。欧洲则大不相同。毫无疑问,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战争准则荡然无存的时候——比如在宗教战争、大革命时期,以及在20世纪极权主义巨头剧烈冲突的时候。即使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各国共存于同一“社会”之中——尽管这还不能算作一个社会,各国领导人对彼此都有清楚的认识——如此,他们便知晓对方的意图,因而避免了矛盾冲突不断升级走向极端 (Hall,1996)。
鼎新也同样非常有力地论述了历史哲学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以及为什么同样的现象没有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这诚然是该书在探讨了中国古代战争之后的第二大主题。中国没有创造出现代世界,也不存在所谓“东方的兴起”,这一点常被视作是中国的失败。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了解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的观点或许会有些益处,这位已故的研究早期伊斯兰历史的伟大学者于25年前在一场关于“欧洲奇迹”的会议结束时,以犀利的言辞表达了她的不满。既然伟大的文明提供的是秩序和安定的生活方式,她诘难道,那么西北欧(Northwestern Europe)——这个动荡不安、群龙无首、暴力冲动不断的地方——就应该被裁决为少年犯了。在她愤怒的背后有着一套成熟的社会演进理论。适应环境带来的是稳定,而进化通常来自边缘、来自失败。这一点对于这个历史哲学上的关键问题也同样适用。该书对中国给了一个恰切的评价,说它是“自我维持”(self-maintaining)的国家(Zhao,2015:341),而相比之下,西方世界则是纷乱无序的。
这并不是说,鼎新对欧洲发展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仅仅是以另一种不同的实际上也还算恰当的眼光来审视它。事实上,他的论述十分优秀,充分运用了四种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后果带来了缝隙中发展的可能性。这里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注意到了现代科学的出现,特别是提及了英国剑桥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对西方兴起的作用。在回应由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Pomeranz,2000)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辩论时,他的论述同样深刻尖锐。他认为,将中国的一个地区和整个英国相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样做忽视了那个地区得以存在的整体政治环境。而他的主要观点则与彭慕兰的截然不同,既清晰明了,又令人信服:在中国古代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限制并塑造了中国后来全部的发展。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