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理学家夏震武及其灵峰精舍弟子是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乡间理学家群体,他们秉持独特的华夷观和“公天下”理想,否定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既不认同君主专制,也不承认民主共和制,隐居山林,笄发古服,践行儒家“三代”理想。但1930年夏震武去世后,其弟子纷纷变服剪发,逐渐分化,其中大部分开始认可国民党政权,成为民国“国民”,后来甚至以儒家的方式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这群近代儒士的认同转变过程绝非线性逻辑所能概括,天下、国家、中学、西学,各种思想因素交织在一起。传统儒家理想一方面是他们拒绝民主共和政府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推动他们接受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源动力。
关键词:夏震武;近代理学;国家认同
近代以来,两千余年颠扑不破的儒家政治理想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之下迅速瓦解,民族国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列文森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这一结论基本合乎中国近代史的大致走向,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基础。但是,同一、单线的思考方式难免会遮蔽掉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歧性,部分学者也对此提出了批评和反思。葛兆光认为,要超越各种概念局限,以更为开放和流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认同与国家意识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宋代之后的中国,诸如天下、夷夏、朝贡和近世民族主义等意识元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杜赞奇主张用“复线的历史”将其它的身份认同和替代性的叙述结构从因果论式的进化史观中解放出来,惟其如此,“我们所听到的不是民族一致而单调的声音,而是一群交互穿插的、矛盾的、含混的声音,彼此之间相互对抗、相互肯定、讨价还价。”

夏震武
天下、夷狄、民族、国家等各种认同,随着时势的变化而流动不居且相互交织。夏震武(1854-1930)及其灵峰精舍弟子在民国时期的表现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过程。夏震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理学家,蒋伯潜曾说:“论者以灵峰之殿清代程朱派的理学,比之章炳麟之殿汉学的古文派,康有为之殿汉学的今文派”。由于近代理学的尴尬处境,这位“理学殿军”长期为学界所漠视,而隐居于乡间的民国旧派士人群体也几乎完全不在目前的近代史书写范畴之内。这群以“复兴三代”为理想的理学家有着相当不合时宜的价值理念,他们既不认同民主共和,也不认同世袭帝制,坚守着儒家的乌托邦,对抗着在他们看来越来越糟糕的世局。不过夏震武殁后,其弟子流散四方,除了继续用传统儒家的天下、华夷观念思考这个世界之外,他们逐渐认同国民党政权,甚至以儒家的方式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夏震武师弟群体政治认同的多歧和流变,体现了近代旧派读书人思想观念嬗变过程的复杂性,为我们考察中国知识人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不拘形式论夷夏”:清遗民?
夏震武一生弟子甚夥,从游时间不一,有的弟子殁于清亡之前,有的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且存世,其内部不可能存在完全统一的价值认同。在学术方面,夏氏师弟门户森严,一主程朱理学,极力排抵陆王心学,但还是有部分门人在其论著中表现出“是王非朱”的倾向。在政治认同方面,差异也相当明显。灵峰弟子张绍价对亡清政权就抱有好感,反对新党的排满之说:“窃谓种族之说,宜随时势为转移,当闭关之世,则汉为同族,满为异族;当交通之世,则又宜以东西洋为异端而引满为同族。”但夏氏另一位弟子王雪庵却对排满复汉颇为热衷,民国元年六月,他在短时间内撰成百二十回小说《神州光复志演义》,将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描写成汉人的光复史,对晚清革命党、秘密会社的排满光复运动推崇备至,其书开篇迳称:“话说狄戎虎视,自昔已然;华夏膻腥,于今为烈……但恨这般番族,恃其凶恶,往往乘我内难,大举入犯,我族剿除不灭,遂为所吞。”同为夏氏门生,张、王二人之分歧不可谓不大。更何况,灵峰精舍弟子遍布全国,乃至日本、朝鲜、越南,生源构成相当复杂,绝不可用生硬的学术谱系,抹消其内部的差异性。当然,他们都团结在其师周围,绝大多数人一生保持对夏氏的高度崇敬,这也是其共性所在。他们普遍奉持传统理学的价值观念,反对西学的过度扩张,对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沦丧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神州光复志演义》
毫无疑问,夏震武对“中华民国”极为排斥。共和制国家在夏氏看来乃是夷狄之制,非华夏所宜采用,这是其抵斥民国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后,他说:“用夷变夏、孔耶合一,以成今日平等自由、革命立宪、废三纲、灭五伦、无父无君、乱贼夷狄禽兽之祸。”革命立宪是用夷变夏之举,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是一个“乱贼夷狄禽兽”之国。他在革命爆发的第一时间就辞去京师大学堂教职,隐居乡里,杜门不出长达二十年。隐居期间,他一度拒绝了浙江都督朱瑞及总统袁世凯的征召,以示对新政权的抗拒。在其影响下,1924年《夏氏宗谱》甚至添入新的祠规,宣布“鼎革之际”族中读书人倘若能“守志不出”,便可照前清举人给胙。这种对民国政权的抵触情绪也反映在其门人身上。夏氏弟子何绍韩在民国浙江颇为活跃,组织各种民间社团,是当时著名的矿业家和绅商,却也表现出逃避政治的倾向,夏震武称许他是:“清社以屋,国变后党派益多,屠沽、贩竖、市侩、佣奴、隶人、走卒、游民,无不思附一党以鱼肉闾阎,而士大夫稍负名誉者,各党必竭力罗致以张其势。东阳何生竞明,浙中知名士,党人欲援以入党而生始终谢绝不许。”
革命后坚持不入城市,隐居灵峰山讲学终老,拒绝使用民国纪年,夏震武的行为与当时的满清遗老颇相似。富阳同乡郁达夫就视其为遗老:“夏灵峰先生虽则只知崇古,不善处今,但是五十年来,像他那样的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也的确是没有第二个人。比较起现在的那些官迷财迷的南满尚书和东洋宦婢来,他的经术言行姑且不必去论它,就是以骨头来称称,我想也要比什么罗三郎郑太郎辈,重到好几百倍。”郁氏在认定夏氏为“亡清遗老”的同时,也察觉到了夏氏与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存在差异。民国初年的清遗老普遍对清复国抱有幻想,罗、郑等人甚至不惜委身“伪满”,为人唾弃。与他们不同,夏震武对清王朝并无好感,对清朝的灭亡也并无惋惜。他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时间(此时清帝尚未逊位)就指出:
政府(指清政府)平日所依重者,非叛则降,非降则逃,全国一辙,无一仗节死义之士。数十年来,是非淆乱,赏罚颠倒,固知其必有今日矣。“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之言于今日益验。而政府粉饰立宪,崇奖叛徒,起用乱臣,至死不悟,哀哉!
夏震武认为,清亡乃是必然之事。他从未觉得有必要为前清守节。在解释自己杜门不出、不事民国这一行为时,他说:“儒者之出处,为道计、为国计、为民计,非为一姓一家计;儒者之守节,为道守、为国守、为民守,非为一姓一家守也。”辛亥革命令夏震武感到悲恸,然而他所悲恸的不是清朝之亡,而是数千年来儒家构建的三代先圣先王之道德理想国的破灭。灵峰精舍弟子认为:“世有称先生为清之遗民者,未足以知先生也”,可谓笃论。
在夏震武眼中,清朝一开始就是夷狄政权,他对清王朝推行编发胡服政策表示了批评。他认为,清朝的编发胡服和民国后的剪发洋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依照儒家华夷观念的标准,这些行为同属非礼之举。他对前清的这种指责,引发了当时部分旧派人士的不满。某人即对灵峰弟子张绍价提出质疑:“《灵峰集》中所最注意者,莫过于编发胡服一语,连篇累牍,竭力发挥,悠谬不胜枚举,谓弟于此等不宜附和,当直言以谏”,他甚至指责“先生(指夏震武)亦系革命一流”。在夏震武看来,已覆亡的清王朝和肇创的中华民国都没有政治合法性。
当然,夏震武以满清为夷狄的观念,与革命派“排满兴汉”的观念有本质的区别。革命派以满人为夷狄的做法,虽部分继承了传统儒家“夷夏之辨”的政治观念,但更大程度上与欧洲19世纪后兴起的强调血缘关系的“族群民族”(Ethno-Nation)关系密切,这一理念强调在人种的基础上界定族群,并由此建立民族国家。而夏震武坚持儒家文化主义立场,其“夷夏之辨”不像革命派一般以种族为界限,他相信“华夏”作为文明中心所具有的涵化能力。为此,他对元朝大儒许衡推崇有加,赞赏许衡“以夏变夷”、将蒙古同化的行为。许衡在历史上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因其出仕异族政权,曾饱受后世儒生诃责。尤其是在明遗民心中,许衡这一入祀孔庙的大儒地位相当低下,王夫之就指责他“鬻道统于夷狄盗贼”,是个十足的“败类之儒”。而夏震武却认为:“鲁斋能令元世祖不改中国冠裳,吾中国人实身受其赐,固不以仕元贬损。”
相较于对许鲁斋的赞赏,夏震武对清儒评价甚低。即便是被视为清代理学名臣的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在夏氏眼中都属于“裂冠毁冕,毁其身体发肤以偷一日之荣”的宵小之辈。这一观念被夏氏弟子所继承,从其弟子张廷琛(字补瑕)及其独子夏成吉合作完成的《续学统》一书中便可见端倪。康熙年间,理学家熊赐履撰成儒学史著作《学统》,该书以程朱理学为准绳,分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五部分,崇程朱,黜杂学,对孔孟以来的学者分门别类进行评价。但此书收录的人物止于明代,清代付之阙如。张廷琛为续补清儒的部分而撰写了《续学统》。该书分内、外二编,内编收录清代宗朱学者,外编则收录汉学、心学、西学等“异端”学者。但外编未完成而张氏亡故,内编由夏成吉进行增补后出版。此书收录人物几乎全部是清儒,但夏成吉在增补此书时,却添入许衡,列于卷首,总领全书。乍观之下,在一部清儒史著作中阑入元儒,相当突兀。夏成吉在解释原因时,先对《学统》作者熊赐履未将鲁斋纳入道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未知熊氏以生长神州之遗民,而不惜编发胡服以立清廷者,其自问果视鲁斋何如也?”他进一步解释:“予校印张补瑕《续学统》,而特补鲁斋以冠清代诸儒之前,既以伤清室之无鲁斋其人,亦望后之君子有天下之责者,以鲁斋为法,毋使五千年炎黄总发种族一朝而竟就绝灭也。”在他眼中,清室没有被儒家礼乐文明完全涵化,是因为汉人士大夫趋炎附势,甘愿“以夷狄之俗变我中国”,致使“先王衣冠”灭绝殆尽。这和革命派认定满洲为夷族的做法,有本质不同。夏成吉斥责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以献媚清室而不耻也”,表面上看与章太炎讥黄氏作《待访录》是“将俟虏之下问”极为相似。实则不然,夏氏基于儒家文化主义立场发论,而章氏则更多地站在一种种族主义立场。
传统儒家的“夷夏之辨”并不是以种族、地域和现实政治作为尺度的,区分夷夏的标准在于其言行能否契合“中国”儒家礼仪,其内在包含了转化的可能性。以华夏为中心、以蛮夷狄戎为外围、同心圆式的“天下”蓝图,构成了夏震武及其弟子对于文明秩序的想象。在他们心目中,放弃中国固有政制模式、效法西方的民主共和国制度无疑是夷狄之政,但未能接受同化、编发胡服的清王朝同样没有统治合法性。既不认同民国,也不认同前清,这就是夏震武灵峰精舍师弟群体在民国面临的尴尬窘境。
二、“总发当年存旧俗”:对儒家理想政治秩序的想象
王明珂认为:“‘服饰’可以说是个人或一个人群‘身体’的延伸;透过此延伸部分,个人或人群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identity),或我群与他群间的区分。”服饰和身体特征乃是人类表达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爆发后,剪辫与留辫成为判定政治认同的方式,“剪辫表示拥护革命,赞成共和,不剪辫表示拥护清朝或者反对革命。”而对于既不赞成共和,又不效忠清室的夏震武来说,无论剪辫或是留辫都显得不合适,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蓄发古装。1912年农历元旦日,已经开始笄发端衣的夏震武写下《自题画像》:“汝冠元冠,汝衣端衣,汝不忍遗体之毁伤而总发以笄,汝朝夕而孳孳者,先圣先王之诗书礼乐,不敢须臾以离,汝幸犹为神州遗民而未化于夷。”古服古装象征着夏震武独特的身份认同,他自视为“黄金时代”的遗民,以恢复儒家“三代之治”为目标,在文章中多次自称“神州遗民”、“三代遗民”、“禹域遗民”,恢复“三代”的服饰和发饰是他践行“三代”理想的途径之一。灵峰精舍弟子也全部追随其师,蓄发古服,隐居问学于灵峰山内,悠游林泉,逃避现代文明,编织着恢复“三代”的美梦。
除了对身体和服饰的关注之外,灵峰精舍师弟群体还致力于恢复儒家古代礼仪。“复礼”是传统儒家重整伦常秩序的主要手段,严格地操演儒家古礼也是夏震武及其弟子们凝聚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霍布斯鲍姆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夏震武等人通过恢复儒家礼仪来反抗西方文明对儒家文明的冲击,他们在灵峰精舍遵照古礼,多次举行祭孔释奠仪式。1920年,夏震武为其子夏成吉举行婚礼,严格采用儒家古礼,并邀请多名灵峰精舍弟子参与和观摩。夏氏弟子刘可培在观摩了婚冠礼全过程之后,颇为兴奋:“曩者欲见先圣先王之礼而不可得,今幸冠昏二礼得复覩三代威仪矣。天生夫子为天下万世维礼也”。一年之后,回到故乡的刘可培模仿震武做法,为自己的次子举行了冠礼仪式。夏震武有诗云:“寒暑更相代,循环理有常。山中存礼乐,世外守冠裳。硕果天心见,潜龙圣德藏。何时非太古,高枕即羲皇”,他们用山中礼乐来逃避现代国家,坚信元运流转,否极泰来,“三代”盛世终会再来。
夏震武等人对“三代”之治还有一整套的制度构想。这套构想立足于儒家“三代”公天下的理想,并掺入了部分近代西方政治学说,最终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世袭帝制、又不同于共和民主的理想政治架构。但是,夏震武政治蓝图的设计并非始于民国。早在1900年创作《人道大义录》一书时,他就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人道大义录》全书一万一千余字,内容涉及反缠足、反纳妾、提倡一夫一妻制等,这些出自一位顽固保守、门户森严的理学家之口,实在令人殊骇。当然,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还是在于它对专制政体和世袭君主制的批判。夏氏提出,认为只要合乎义的原则,君主是可以被离弃、废黜乃至于诛杀的。他剥夺了君主作为“天子”的神圣身份,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君主的产生进行了解释:
民不能自治而举一人以立于万民之上,畀以生杀黜陟之权,率天下以受治于其下,则非以天下私一人,固将责以生养而安全之焉。君受生杀黜陟之权于民,为天下兴利除害,必劳苦什伯千万于民,立法行政,无一不出于民心之公,而后可以立于民之上。民者,君所受命者也;君者,民所托命者也……天下者,万姓之天下,非一姓所得私也。
在夏震武眼中,君位非神授,实由百姓赐予,乃天下公器。他一再强调君主由民众公立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民众认可的贤者才具有成为君主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他褒扬了三代时期的制度,并认为自尧舜殁后,真正的君道就已灭绝,秦汉以降的所有君主均不过是“私天下”的产物。他提倡,中国政制应当回到三代时“传贤不传子”式的“公天下”状态,同时,必须在制度上保证“君民一体”的运作模式,避免君主独裁,以民众参政的方式来分割君权,“杀人由众议之,君不得专杀一人;财由众议之,君不得妄用一财;举官由众议之,君不得擅举一官。专焉、妄焉、擅焉则法乱。乱法者,轻则废,重则诛”。这种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孟子的“君末民本”思想,更近似于西方的主权在民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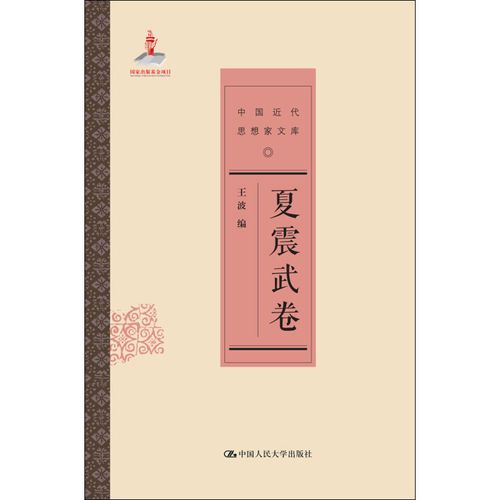
夏震武文集
夏震武对家天下状态下的君主个人素质表示了极大怀疑。他认为,“汤武不世出而桀纣接踵,伊霍不世出而太甲、昌邑接踵”,世袭制产生昏君暴主的可能太大,最终天下万姓备受荼毒。正是基于这种“幽暗意识”,夏氏主张恢复三代传贤之制,废除世袭专制,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正本”之法:“三代以下,立一法生一弊,纷纷言治者皆末也。正其本,万事理矣”。他进而提出,君臣关系要因时而变,不可迂腐拘泥,当君主贤明时,臣子要辅政、直谏;当君主昏聩时,臣子要革命、易位,“公天下而放伐废立者,忠臣义士为之”。夏氏创造性地将放伐废立、革命易位纳入了君臣之义中,几乎完全破除了君王身份的不可动摇性和神圣性。
夏震武甚至支持在中国推行西式议会制度,并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乃是三代之遗制。对此,另一位保守派人物胡思敬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致书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称:“君子不为已甚,甚则绝人向善之心,将悍然操戈而与吾道为敌,亦吾党所深惧也。夏伯定《人道大义录》敬寄一册奉览,此公竟发狂疾!”面对胡氏的严厉指责,夏震武亦致书刘廷琛作为回应,他说道:
胡君必以议院西法,在所不取,则亦将举谋及庶人、致询万民、乡举里选、三代古制而尽去之矣。反斯世于三代,其将何道之从?吾甚惑焉……议院可以制暴君昏主,胡君亦既知之矣。天下暴君昏主多而贤主少,则议院固未尝无利于民,何必废之?
不惟如此,夏氏甚至认为,在议员的产生方式上,应当放弃间接选举(复选),而采用直接选举(单选):“单选不能尽人运动,犹有公论存焉,复选则乡党自好之士无肯应选,投票者类皆把持公事、武断乡曲之绅董,公论绝矣”。即便是新派人物梁启超在面临此问题时,也认为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只宜采取较稳妥的复式选举:“选举人之智能不足,诚不免有所缺乏之感……惟有间接制可以略矫此弊”。夏、梁二人同样在宣统二年(1910)发表此番言论,但无疑夏氏在想法上比梁氏更为大胆,而梁氏则更为谨慎。激进抑或保守,未可以人物之新、旧论之。
以儒家“三代”公天下标准为绳矩,则现实的王朝或国家当然令人失望,而夏震武也并没有对现实的君主或国家领袖产生过效忠意识。当晚清时,夏氏曾怂恿其座师徐致祥上疏奏请朝廷为光绪帝立储,1900年“己亥建储”立溥儁为大阿哥,夏氏因此被征召起用。溥儁被废后,甘肃提督董福祥阴谋奉其为监国,定都西安,并延请夏氏执掌内政,但夏氏断然拒绝。在解释夏氏拒绝原因时,其同门许正衡称:“灵峰尊孟氏‘民为贵’之说,宁肯拘于一姓,且异族哉?”没有道统合法性的“一姓”君主,不可能获得夏氏的认同。王汎森指出,清末国粹“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夏震武唤醒儒家“三代”的历史记忆,实际上是将儒家尧舜禹汤之“道统”与现实的君主或总统进行分离,借用三代“天下为公”这一儒家天下观来否定任何现实政权的政统合法性。
夏震武激进的“公天下”理论被其大部分学生所接受,灵峰弟子甚至标举《人道大义录》为“六经之后第一篇”,孙乃瑶在致信给灵峰精舍同门管赞程时,就对该书赞誉有加:“吾师《人道大义录》议论多属开创而实本乎经,责备上逮前圣而不诡于正,足下所谓破二千年之愚忠愚孝,俾有志之士探讨服行而不失其中,如出于三代之前者,真知言哉。”夏震武及其弟子以“三代”天下理念,对现实政权进行排斥,他们既不愿意做清遗民,也不愿意做民国国民,有着怪异的装束和发饰,怀抱着民国时人难以理解的政治理想,与那个时代几乎完全脱节。震武殁后,灵峰精舍迅速解体,一位记者游览了精舍故址后,写道:“我曾看过那书院的一张团体照,几乎疑心是一群道士在拜忏呢。”
三、“画图疑作古人看”:民族国家观念的逐步形成
民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这一反传统浪潮的兴起之后,已经将儒家思想视为造成国家落后的祸根。在此光景下,灵峰精舍师弟依旧幻想着恢复三代之治,在外界看来无疑是天方夜谭。夏震武去世前,笄发端衣的美梦已经开始渐渐瓦解。1928年,灵峰弟子何绍韩(字竞明)对于束发古服提出了质疑,“有竞明所作《说服》一篇,对于总发古服略有评论,精舍同学以为违戾师说”。尽管精舍弟子对是否应当翦发存在异议,但同年,夏震武最亲密的弟子朱天存却决定翦发并“变服出游”。对此,震武任其为之,只是告诫他:“总发者,吾神州之旧俗,必不得已而翦发,但不可忘其所以耳。”朱天存也安慰其师称,翦发改装只是从权之举,为的是“接近民物”,而儒家的纲常名教,则时刻牢记,不会推诿背弃。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外观的改变只是第一步,弟子们将慢慢背弃老师的信念,在心理上从一名儒士转变成国家的国民。
灵峰弟子们在夏震武殁后,翦发出山,从事各种职业,他们从最初极力否定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到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忠实拥趸。夏震武弟子叶梦麟(1895-1987)曾于1920年代后期,奉师命掌教山东周村的灵峰精舍第一分舍。分舍建成次年,地方政府教育科要求在分舍中增添国民党党义课,叶氏在得到夏震武“宁可停办,也不能添党义课”的指示后,毅然停办分舍。但是,拒绝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叶梦麟在其师去世后,却“加入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敬仰总理为神圣的民族救星”,并担任国民党高官陈诚的机要秘书。叶梦麟晚年曾撰有一副名为《群圣穷通》的楹联:“尧舜禹汤文武周孙蒋陈达而在上,孔颜曾思孟周程张朱夏穷而在下”。从下联可以看出,叶梦麟将其师夏震武视为道学谱系的传承者,这点无甚骇观。令人惊讶的是,他在上联中将孙中山、蒋介石和陈诚视为儒家“三代”圣王和理想政治家们的继承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建国理论中本就包含了相当多的儒家思想元素,蒋介石进一步将三民主义原理儒学化,这或许在客观上促进了灵峰精舍弟子对民国政府产生认同感。
而灵峰弟子刘百闵(1898~1969)变服出游后,不出十年,便成为了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宣传骨干,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指导处长、中国文化服务总社社长、国民参政会参议院等职。刘百闵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曾与马一浮一道创办复兴书院,并且是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主要合作人,毕生保持着对震武的尊重,在晚年所撰《周易事理通义》一书的扉页上,他题写到:“本书敬以纪念先师灵峰夏先生逝世三十五年教育之恩。先师严气正性,泰山岩岩气象,如在羹墙,未尝忘也。”刘百闵和叶梦麟一样,至于晚年,犹拳拳难忘自己灵峰门人的身份,但与夏震武坚决否定民国的合法性不同,他们已经放弃传统的“华夷之辨”,接受了民主共和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作为国民党的重要宣传骨干,刘百闵公开宣扬“民族政党”理论,认为国民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合法政党,鼓吹一党专政。在一篇1938年的文章中,刘百闵称:“本来一部人类进化史,就是一部斗争史,最初为人与兽争,继则人与人争,现在是人与自然争、科学争的时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的定律……我们不能适存这人与科学争的世界,能不能演进到人与科学争的境地,这个伟大的时代就是试验我们评判我们的机会。”在日寇的侵凌之下,儒家已经无力开出救世药方,国家主义、科学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几乎无处不在,只有这些新的“主义”才能带给中国新的希望,建立新的文化自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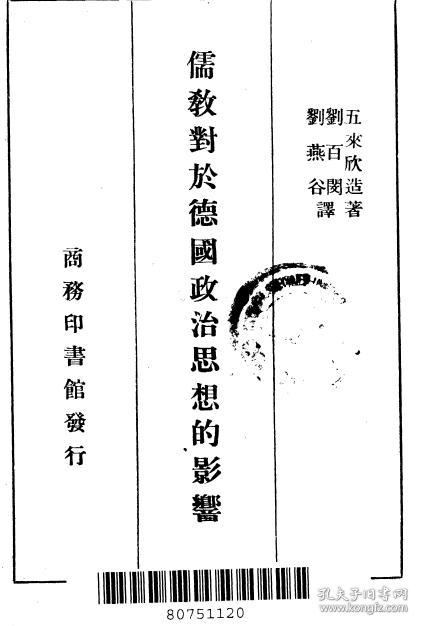
《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终其一生,刘百闵都坚持认为儒学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具有极重要之地位。他翻译并出版了日本人五来欣造的《儒教对于德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一书,相信儒学对西方近代政治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西文明之间存在接榫和对话的空间。但他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已经和其师夏震武所信奉的、可以执一御万并拥有绝对价值的儒家思想相去甚远。刘氏称:
在具有类似的民生状态而又有先进和后期区别的两国间,文化上的影响是一面的;即先进国影响后起国,而后起国不能影响先进国……我们认为:儒教影响于德国政治思想,开始于莱白尼兹,普及于华尔夫,实现于腓特烈大帝,至威廉第二而消灭,代之而支配德国政治思想的,已不是儒教而成了罗马帝国时代的西洋固有的征服精神。
他明显受当时风靡一时的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文化的迁移和传播是建立在国家力量强弱对比这一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传播论带有浓厚的社会进化论色彩和帝国主义文化扩张的意味,其背后贯穿着民族国家互相竞争的价值理念,与儒家同心圆式的天下观相去甚远。
灵峰弟子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呈现出“流质易变”的面貌,这在朱天存(1896-1952)保留下来的日记中得到了最细致的印证。1931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迫于生计的朱天存一直处于游幕生涯之中,先后供职于湖南和福建省政府。最初,以儒士自许的朱天存对民国政府并无任何好感,多次为无奈出仕而感慨纠结,194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予之仕途连蹇,亦不自今日始也。曩在三湘,主人(指湖南省主席何键)颇似道家而好虚声;今在八闽,主人(指福建省主席陈仪)颇似法家而好少年。予虽不学,然亦有其宗旨,不肯以己殉人。……士君子学不通时,方枘圆凿,既不肯曲学阿世,则修其天爵,以仕为隐,搏升斗之禄,游戏三昧。”士君子总发深衣时的抱负,在现代国家体制中难以舒展,失落与愤懑可想而知:“其时总发深衣,高睨大谈,亦有推倒一时之概。今何如乎?十年仕宦,寸□未展,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朱天存对国民党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抵触,直接地反映在他对国民政府政治仪式的不屑态度上。1936年元旦,民国成立纪念日,各级政府按照法令规定,进行“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等仪式,但在这一天,朱天存在日记中写道:“军政党各机关在中山堂集合团拜,予不往,在廨温酒一瓯,诵苏陆诗以自遣。下午至天心阁眺望,高台悲风,万木尽凋,若无人矣。”儒士遗世独立、不落俗流之情溢于言表。在同年参加完一场总理纪念周活动后,他调侃称:“初四日,照例列席纪念周,(此处涂去三字,按文意,当指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皆著草黄色制服,满目苍黄,尽食民间脂膏,予亦小蝗虫之一也,思之汗泚”。腐败与荒诞感冲淡了政治仪式本应有的庄严和肃穆。朱天存在心理上抵制孙中山崇拜,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民族国家“新国民”身份的一种不适应。此外,朱氏对国民政府推动的孔子崇拜也相当不屑。1938年,在参加完一场省府举办的孔子诞辰纪念会后,他写道:“会场中对孔子稍有认识者,惟予而已。中山在尼山之上,法家谈儒家之言,宜其不合也。回忆曩日在精舍释奠,恍如隔世,国乱家贫,天涯乞食,虫沙猿鹤,宇宙茫茫,自叹为黄帝不肖子孙而已。”陈蕴茜认为:“南京政府在全国再度兴起孔子崇拜热,目的是利用孔子崇拜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为蒋介石推行一党训政和个人集权服务。”对于这种脱离儒家语境、完全沦为政党意识形态工具的孔子崇拜形式,朱天存显然无法接受。在1939年的孔子诞辰纪念日前一日,他感慨道:“清末革命志士鉴于社会政治之腐败,迁怒于孔子,章炳麟、蔡元培之流,掊击不遗余力,酿至五四运动竟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其父杀人,其子行劫,俎豆钟鼓、神龛栗主,摧毁无余。至今二十二省九百余县中,欲求一完整之文庙不可复得。纪念云乎哉?”
但是,在1942-1943年之间,朱天存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慢慢发生转变。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朱天存在其日记中持续记录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最新战况,显示了他对民族危亡和国土沦丧的焦虑。战争持续五六年后,胜利的曙光尚未完全出现,在一种充满民族危机感的氛围中,朱氏在理智和情感方面,都慢慢倒向了在当时主持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在1943年8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使非有蒋总裁新生活运动,掇拾于孙总理民族主义薪火之中,大声提倡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为人类尽仁爱,为世界尽信义和平,则此次全民抗战,将操何术以御之?”他开始相信,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念将支持中国抗战走向胜利。而且在此之前,朱氏日记中对蒋介石径称以“蒋氏”、“蒋介石”,在1943-45年的日记中,全部改为“蒋总裁”、“蒋委员长”或“蒋总统”,这体现了他对蒋介石个人态度的转变。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抗战领导人的形象进一步抬升,朱天存对蒋氏的崇拜也随之提高:“世界正义,乃由美故总统罗斯福而重光,杜鲁门、丘吉尔及我蒋委员长诚全世界之救星矣。”在朱氏心目中,蒋介石已经成为和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齐名,他们一起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役的胜利,维护了世界正义。
当然,朱天存对国民政府的认同和信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随着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持续腐败和无能,以及在国共战争中的节节败退,朱氏在政治认同上,慢慢倒向共产党一方,而共产主义是之前灵峰精舍弟子所极力排挞的。原本在灵峰弟子口中“乱甚于战国,祸酷于暴秦”的共产主义思想,在朱天存眼中发生了变化。1949年1月,他在看到毛泽东为答复蒋介石《元旦和平公告》所作的时局声明后,感慨称:
中国古代社会本来是均产制度,一夫授田百亩,及老而还,田未尝封己自私也,制禄仅足以代耕,未尝剥民自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则变置,未尝以爵位世袭传子也。政府贪污残暴,则有革命之义,有易位之义,有共和行政之义。秦汉以降,专制世袭,此义不明,天下为公,徒托空言。孙中山弘览古今,阐明大同之理,马克斯列宁亦有鉴于此世袭封建之祸,提倡社会学说、共产主义。
夏震武的“公天下”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在朱天存的思维世界中奇怪地扭合在了一起。反对爵位世袭和专制王权,凸显“革命之义”和“易位之义”,这些原本都是夏震武《人道大义录》对于“三代”理想天下秩序的设想,但却被朱天存用来与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类比。另外,夏震武曾大力宣扬井田制,并制定实施方案,灵峰精舍弟子更是前往西北垦荒,实验井田制的可行性,对于土地公有和“耕者有其田”抱有极大的幻想。怀有这种乌托邦情愫的士人的确会因为共产主义的“均产制度”而对其产生认同感。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9日,朱天存从书铺买了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阅后,他写了一篇极长的读后感。在这篇读后感中,他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并完全接受了新政权:
中国国民党主政二十余年,其大病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没有革命的彻底性,所以至今为群众抛弃,变成向隅的可怜虫了。现在共产党的军事快胜利了,政权亦快要到手了,这一份破落的家当,老大不争气,听信妇人及小人之言,弄到如此田地,现在要看看老二的手段了。老二现在所发表振顿家门的理论,是对的,希望老二要彻底,要实践,要有丈夫气。不要听信枕边之言,不要依靠左邻苏大伯伯之力,苏大伯伯与山姆叔是一样,要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的。
这是朱天存留下的所有文字中,唯一的白话文,新旧交替之际情绪与观念之波动,于此亦可见一斑。
1930年后的朱天存,从一名不依傍任何政权、只信奉儒家“三代”公天下理想的士大夫,慢慢开始认同民国,到最后接受共产主义新中国,其政治认同随着时势的转移而不断发生变易。但这并不表示他完全是个随波逐流之人:对蒋介石产生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氏提倡的“忠爱礼义廉耻”符合儒家的道德审美;接受共产主义,是因为其政治口号和土地政策契合了儒家“公天下”的社会政治理想;即便是1949年接受了新中国政权,但他对共产党提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之类的言论颇为不平,辩称“孔子非封建主义者”。可见朱天存维护儒家尊严的意志并未受政治局势转移的影响。
四、结语
夏震武及其灵峰精舍弟子秉持着儒家的“华夷之辨”传统,并坚持富有特色的“三代”公天下观念。他们对清王朝和中华民国都采取了否定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儒家独立于政治之外又高于政治的“道统”对现实“政统”的批判传统。但是,儒教的式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发展不可逆转之趋势。随着精神领袖的去世,灵峰弟子在剪发变装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放弃原来所坚持的华夷观念和“公天下”理想,开始更多地用民族国家的惯用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在心理认同上成为一名“新国民”。
以赛亚·柏林认为:“每个时代、每一群人乃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而且这些视角并非固定的,而是在变化,这点只有从我们自有的证据来理解,这里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上的、现成的最后证明可供使用。”人类思想活动充满流动性,本无规律可循。近代民族国家思维并不能完全取代儒家信仰,二者呈现一种交织的关系。面对清王朝,面对中华民国,面对共产党政权,灵峰弟子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政治认同随着世势的转移而变动不居,传统读书人根本无法保持纯粹的单一认同,在古/今、中/西二元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间不断游走。这个长期被大历史叙事所遮蔽的边缘群体,为我们观察传统知识分子从天下认同转向国家认同这一复杂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十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92-105。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