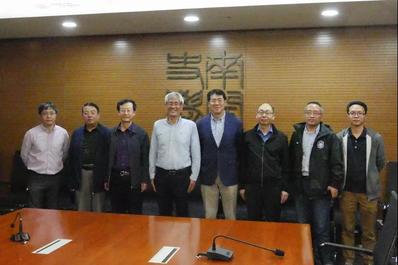4月22日,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郑振满做客南开大学第十三届历史文化节“述往·知来”大讲堂,在历史学院院楼127会议室进行了题为“从民间社会研究中国历史”的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张思、卞利、副教授张传勇,讲师张岩,哲学院副教授卢兴以及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罗艳春与会,学院本硕博学生共一百余人参加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主持人常建华教授首先对主讲人进行了介绍,并对郑振满教授此次应邀参与南开大学历史文化节表示热烈欢迎,讲座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

郑振满教授首先对此次讲座的内容提纲挈领地进行了介绍。讲座以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内容,围绕中国传统史学的误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三大模块展开。
郑振满教授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谈起,指出在中国古代,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对于史书的研究,但中国古代的史书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并不具备独立性,古代的官方史书大多关注的是王朝兴衰的问题,很少涉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并且,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包括官方史书在内的传世文献往往会被修改,所以仅仅依靠这些史料,是很难了解到历史的真相的。随后,郑振满教授指出,中国传统人口与土地的统计数据中存在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的数据可以被史学研究者利用,去研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而要做好这些研究,就要到民间去,深入到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去发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维逻辑,寻找到民间应对政府统治的策略。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科学体系的进入,很多学者提出应当走出“王朝体系”,并进一步产生了“新史学”。部分学者学习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致力于新史料的发现;部分学者使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历史问题,而这一思潮也影响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接着,郑振满教授指出中国现在的通史体系是按照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逻辑来建构的,但套用欧洲社会五大阶段的解释方式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不利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恩格斯曾提出,欧洲社会的五大阶段并不应该套用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第三国际当时也曾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应当采取怎样的革命策略进行了讨论。而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则是根据当时面对的现实问题所确定的,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基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区”的反思,郑振满教授围绕中国历史的多元结构展开了讨论。他以傅衣凌先生的遗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为切入点,此文指出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明体系,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社会在较长的时段内都是多种经济形态、生产方式并存的状况。欧洲国家的社会形态转变大多都有较为明确的标志性事件,它们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划线分割的,但中国不同。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王朝国家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形态。傅衣凌先生提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有公、私两大系统,国家是“公”的系统,而实际统治社会的是“私”的系统。私的系统是地方的、民间的制度,是地缘与血缘的密切结合,地域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第二大模块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振满教授把该模块分为傅衣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讨会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讲述。郑振满教授首先回顾了傅衣凌先生的学术历程,指出他先后接受过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后来创立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1939年,他在福建永安的一座老宅里发现了一箱契约文书,开始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傅先生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版了《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明清商人与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等著作,并且提出了以民间文献、乡规俗例、实物碑刻证史的治史方法。此外,傅先生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研究资料的积累与人才的培养亦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后,郑振满教授针对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依次阐述了福建、广东、江南等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并介绍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讨会的基本情况。该会议于1987年在深圳召开,是中国史研究领域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海内外众多学者与会,提出了许多富有导向性与前瞻性的主张,如注重区域研究、社会实体与计量分析,对后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指引意义。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模块,郑振满教授提到了四次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计划或组织。在华南传统社会文化研究计划(1990-1994)中,学者们致力于标志性的社会文化遗存和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诸多学术成就。1995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华南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研讨会会上,开始形成以宗族、庙宇为中心的研究取向。2003-2018年举办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组织学员到现场读文献,寻找王朝国家与区域社会的联结方式,后来被归结为“进村找庙、进庙读碑”。最后是科大卫教授主持的香港卓越学科领域研究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从2010年到2017年,前后历时八年,培养了许多青年学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快速发展。
最后,郑振满教授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进行了概括,即回到历史现场、注重社会实践、跨学科研究视野。回到历史现场不仅仅是为了找资料、读资料,更重要的是回归人性,从当事人的立场来想问题,思考他们的应对策略。这种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可以对近代外来的科学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郑振满教授提到,田野是思想的实验室,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起到检验学术思想的作用。“跨学科研究视野”则是指学者个人应当具备不同学科的理论素养,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总之,回到历史现场,从民间的社会实践去重新思考中国历史,提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的学术追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后,主持人常建华教授对郑振满教授表示了感谢,并对讲座内容作了简要总结。
在讨论和提问环节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生刘曦泽提问,应当如何看待将人造建筑放到特定的空间去阐释其历史内涵这一问题。郑振满教授回答到,民间建筑与仪式系统的存在,可以维持共同体的持续运作。民间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应该从特定的空间去阐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生黄裕茂提问,客家人族谱中有载录郎名的传统,但到元末明初时,一部分族谱中的郎名消失,且非客家群体的族谱中也载有郎名,应当如何看待这些现象?郑振满教授认为,郎名在元末明初消失,可能和里甲的户籍制度有关,户籍立户时,郎名对于个体的区别度较低,因而被官名所替代。族谱中载有郎名的传统,不必纠结于客家与非客家群体这一问题。一般认为,族谱载录郎名的现象,首先出现在畲族当中,其后才是客家人与福佬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本科生刘研博就虚拟宗族的概念进行提问。郑振满教授讲到,社会生活中存在合作关系的人并不限于宗族成员,但在当时社会,有主流话语权和合法地位的是宗族,这就使得没有宗族的人有了伪造宗族的必要。在福建就有很多通过《文献通考》等文献资料构建起来的虚拟宗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宋培源提问,礼仪标签,结构过程,逆推顺述这三个理念的所适用的研究时间上限是否可以前推?郑振满教授认为,在更早的时期内运用这三个理念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因为它们需要到民间寻找资料,所以运用于更早的时期会受到限制。同时,这三个理念,是为了应对现实问题,在具体语境中提出的,研究的思路不应该被它们所局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本科生刘其远提问,应当如何看待台湾学者王明珂对于民族史的看法,以及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社会文化的科大卫模式与丁荷生模式?郑振满教授认为,民族学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历史人类学的,但王老师的研究相对来说不是过程性研究,早期民族史与现代民族史的连接较为薄弱。就科大卫模式与丁荷生模式而言,前者更注重国家的政治权力,而后者更注重的是文化与宗教因素。
随后,郑振满教授和与会学者进行交流。张思教授提到,我们所构建的历史理论体系中,王朝理论和史官理论带有“《资治通鉴》”的色彩,而从民间视角进行的历史研究,对上述体系是非常重要的补充。郑振满教授谈到,当我们从民间角度去理解“我们的国家”时,就会发现传统的国家在地方有不同的存在形态。传统国家也会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统治策略,而地方统治经验也会推动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与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都应当从民间的层面去理解。
随后,张思教授与郑振满教授讨论应当如何避免进庙读碑即判断此地有国家因素这样草率的行为。郑振满教授认为,民间社会研究需要制度史和通史的知识储备,否则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研究难以深入。与此同时,国家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形态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一个完整的中国十分重要。
余新忠教授就郑振满教授针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提出的相关意见谈了自己的感悟:历史学家早期的现代科学研究,来自于西方的理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就会发现从文献、理论出发的研究与历史上的人是有距离感的,但郑振满教授从民间视角出发的研究是清晰而透彻的。余新忠教授认为,医疗史的研究,同样应该深入到民间情景、放至相应地域中去,而这就需要寻找民间的医疗知识,收集民间的医疗文献。郑振满教授也对余新忠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表示应当回归到人的生存状态去思考历史问题。
最后,讲师张岩向郑振满教授请教“研究同质化”的问题,郑振满教授回答到,不应树立得出具有普适解释力理论的预期,从个案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借助新的资料讲好个体故事同样也是成功。
伴随着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南開史學」公眾號,2021年5月20日。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