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索(1982—1984年)
1982年夏天,我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立刻面临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继续升学或当兵。后来,我选择入伍担任预备军官,但仍保留了历史研究所的入学资格。
当兵是无可逃避的“义务”,也是体魄与心智的锻炼。在文学院浸泡了四年,心灵自由而奔放,生活随意而自在,因此,在入伍之后,格外难以忍受讲求权威、服从、标准、齐一的军人文化。而且,当时还在“戒严”时期,言论、思想与行动几乎都戴上了手铐与脚镣。役期一年十个月,苦闷中慢慢煎熬。所幸我是少尉经理官,担任补给和管理的工作,较为轻松,而且还有独立的卧室,在半是禁闭的状态下,读书成为最好的解脱。
那时,我带了王守仁(1472—1529年)的《阳明全书》和葛洪(约284—363年)的《抱朴子》到部队。我特别挑没有标点的版本,一个字一个字点读,在断句的过程中,仿佛吐纳一般,呼吸着儒、道二家的思想。我先是读王阳明,因为我大学时代的志业是彬彬的儒者。但是,越读越无聊,纸面上充斥着天、人、性、命、道、理、心、良知、格物这一类的字眼,以及一篇又一篇的问答、书信、序文,反复围绕着仁义道德与学问事功。我非常佩服,但如坠五里雾中。
后来读《抱朴子》,一看,眼界大开,惊愕连连。葛洪所描述的道教的世界实在太有趣了,有炼金、房中、辟兵、禁咒、长生、神仙、隐形、分身、变形等法术,提供了各种欲望的满足方法。对于神仙之说,我虽然不敢置信,但仍被勾引起一丝富贵不死、法力无边的贪念。更重要的是,童年时期在乡村的一些经验突然醒觉,我恍惚又听见了道士在丧礼中的摇铃声、吹角声、唱诵声,看见了三清道祖、十殿阎王、地狱鬼怪的图像。在阅读、冥想的过程中,我逐渐找到当下与往昔的联系,也找到自己历史研究的方向。
我选择宗教作为主战场。原本打算从中国道教史入手,但是,当时我所能读到的只有许地山(1894—1941年)、傅勤家、孙克宽(1905—1993年)、李丰楙四人的著作,而他们在讨论道教起源的时候,都提到道士与巫觋有紧密的关系,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所碰到的童乩。
20世纪60年代,我所生长的滨海村庄(台湾云林县台西乡五港村瓦厝),还相当“落后”,没有象征“现代文明”的自来水、汽车和医生,多的是苍蝇、流氓和沙眼。病痛的时候,通常会求助于童乩,降神、问卜、画符、念咒、收惊、叫魂、祭解、驱邪,无所不用。而我的表姨丈就是村里最神气的童乩。事实上,我还有一位姨丈、两位表哥、一位堂哥,也都是童乩。我对于这样的人并不陌生,他们应该就是传统文献所说的巫者。
可是,根据《国语·楚语》的记载,巫者在古代是圣、智、聪、明的才艺之士,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而童乩在当代社会却受人轻贱,被人打压。官方与主流媒体不断宣称他们是低级、野蛮、邪恶的神棍,应该予以禁断。在知识的殿堂中,他们更是毫无立足之地,很少有人愿意碰触或讨论这样的人。因此,我很快就决定要探索巫者的古今之变。我的终极关怀,不是陌生的巫者的往日光辉,而是我所熟识的童乩的当代困境。

台大校园
二、启程(1984—1987年)
1984年夏秋之际,我服完兵役,重返台大校园。一开始,野心勃勃,企图以“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巫者”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并获杜正胜先生(1944—)与韩复智先生(1930—2014年)二位老师首肯,同意联合指导。但是,到了1986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之后,我不得不限缩自己的研究范围。我知道自己在先秦史的领域,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有所成就。我虽然可以通读传世文献,但对于古文字学、器物学、考古学、出土文献却所知有限,而材料的取得也相当困难。因此,在1987年是以“汉代的巫者”为题完成学位论文。
这篇硕士论文主要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勾勒汉代巫者的面貌。我先是疏解“巫”的字义,接着探讨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说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然后分析巫者的技能(“巫术”)和职事的内容,借以解释巫者活动的主要凭借,以及他们的社会功能。而为了检验汉人在观念上是否能接受“巫术”,便解析巫者施行巫术的观念基础,并探讨汉人对于鬼神和祸福之事的看法。紧接着,评估巫者的社会影响力,厘清巫者的活动范围,探讨他们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地区的活动情形,借以说明当时巫者所触及的“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最后则是总论巫者在汉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年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我所能凭借的前人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因此,只能在史料方面多下工夫。无论是传世的典籍、碑刻,新出土的简牍、帛书,还是非文字性的材料(包括铜镜、画像石、壁画、帛画、墓葬、建筑遗存等),我都竭尽所能,逐一检视、爬梳、分析,从而重建我所认知的汉代巫者的世界。我所走的似乎是所谓“史料学派”的老路子,一切以史料为依归,多做考证、叙述,少做诠释、臆解。
不过,那时候台湾正大力引进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我不免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布劳岱尔(F. Braudel,1902—1985年)对于“时间”的界定、对于“心态”(mentalité)的强调、对于“历史整体”(histoire totale)的观照,以及他们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径,更引导了我的思维。此外,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的学说,也都或隐或显地左右了我的论述。

布洛赫(Marc Bloch)
三、闭关(1987—1989年)
或许是我的硕士论文还有点原创性的价值,或许是因为杜正胜先生(以下称杜先生)的荐举,我从硕士班毕业之后,随即获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1987—1995年)。
当时的史语所还是四组一室的编制,我隶属于人类学组,是最年轻的一位小学徒。当时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不算太多,也不特别受到重视,但是,杜先生“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最好是到海外留学。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又是人类学组的主任,算是我的主管兼导师,我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或正当性。因此,我刚一进所,其实就已经在准备出国进修。
出国以前,我还有两年的时间(1987—1989年)。除了强化英文能力、申请学校之外,我也开始为自己后续的学术发展做准备,虽然时间不长,但如今想来,却是非常重要。
那是一段精神专注、心灵活跃的日子。我几乎参与了史语所每一场讲论会和演讲活动,接受了多元学科及不同知识传统的洗礼。史语所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所,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字学,拥有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那时候,一些学界知名的老前辈都还在,中壮年的学者已卓然独立,此外,还有一大批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生力军,以及一些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助理研究员,其他的研究人员也都学有专精,博学广闻。成员的世代差异极大,最老者已逾九十岁,年轻者还不到三十岁,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大家的学术背景也很不一样,有的是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等名校,有的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所养成者,有的是刚从欧美各国的名校回来的,也有的是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可谓济济多士!这样一个多元、多样、异质的团体,在知识的论辩上便显得相当激烈。当时,大约每两周就会有一场演讲。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报告,另外一个小时讨论,文稿都是先前就印给所有同仁。因此,在讲论会上常见刀光剑影,各种新旧的概念、理论、方法、意见都有人提出来,或是客气的商量,或是赤裸裸的批评。两年的聆听,在各种思潮、论述、风范的冲击下,我知道治学必须有壮阔的心胸,不能拘泥于一方,不能自傲、自满。他们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聆听各家说法并没有让我迷失自己的方向。在阅读方面,我选择了三个面向。我过去已读过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以秦汉史为治学的重心,但我不想成为断代史的专家,通读历代史籍是必修的功课,因此,开始读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正史”,延长自己的时间纵深。其次,我的初衷是要研究道教史,必须克服道经研究的难题,所以挑了道教最早的一部书《太平经》,进行精读,这也是争议相当多的一部书,所以,便顺便搜集、阅读各家的研究成果。此外,为了快速掌握道藏的梗概,也开始读《云笈七签》,并构思一些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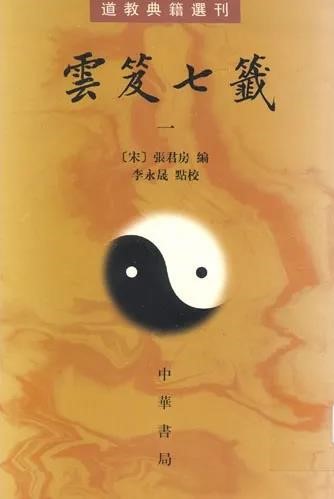
《云笈七签》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要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似乎不能不碰敦煌文献。但是,当年的敦煌文书很难阅读,用微卷翻印的字体很不清楚,只能看日本整理、出版的一些道经。幸运的是,那时中国大陆已将敦煌壁画、艺术方面的材料以较精美的方式印制出版,所以我转而花费较长的时间在图像学的研究,并透过敦煌艺术进入佛教世界。更幸运的是,台湾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的“戒严令”,在这之后,原本被管制的一些书刊,才能自由借阅、购买、阅读、引述,我也才能逐渐接触、熟悉来自大陆学人的著作。
四、留学(1989—1994年)
1989年,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那时,我同时获得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以下简称普大)博士班的入学许可。若到哈佛,可以跟随张光直(1931—2001年)教授,强化人类学的训练。若到普林斯顿,可以师从余英时教授(1930—,以下称余先生),仍以历史学为专业。他们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也都见过面,谈过话。不过,我从大一开始就读余先生的著作,比较熟悉他的学风,深受他的启发,因此,在多方考量、几经波折之后,我最终选择到普大。
普大的留学生涯,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9到1991年,在这两年之间,我修完所有必修、必选的课程,通过两门外语(日文、法文)的课程修习和测验,并赴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短期游学。第二个阶段,从1991到1992年,大约一年时间,我完成了学科考试,主科是余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副科是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年)教授的中国中古史,以及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教授的中国宗教。第三个阶段是在1992年,通过学科考试之后,大约两个月之内,我提出了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并获通过。第四个阶段,从1992到1994年,大约两年时间,我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答辩、修改与缴交,并获得学位。
我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3rd-6th Century A.D.)”(《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巫者与巫俗》),这其实并不是我最初要探讨的课题。我当初申请赴美留学时,因刚读罢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对于他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探讨瘟疫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深感佩服,但对于他书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叙述,觉得过于简略,而我在硕士班的阶段,除了宗教史之外,另一个研究兴趣是疾病史(身体史),因此,我便以“汉代的疾病观念”为题撰写研究计划,打算在美期间能专攻疾病史。可是,到了普大才知道,历史系虽以科学史研究闻名,疾病史却非其主流,而东亚系的杜希德教授虽曾发表过东亚瘟疫史的论文,但非其主要兴趣,图书馆的相关藏书也以中国传统的医籍为主,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著不多。所以,我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回归宗教史研究的方向,并以历史系、东亚系和宗教系的课程为主修。
在摸索的过程之中,我曾到艺术与考古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人类学系旁听一些课程,激发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有一阵子曾经想以“梦的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篇”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连续几个课程的学期报告都围绕着这个课题撰写。我当初的想法很天真。我认为睡眠的时间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而做梦又占了睡觉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人类历史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睡眠史,十二分之一写梦的历史。不过,这个题目并未获得指导教授余先生的首肯,他似乎是认为“清醒的世界”比较重要,而且,要进行“梦的历史研究”,必须有谨严的概念架构,并分疏、整合许多不同的理论工具,不容易落实。
放弃梦的题目之后,我很快就决定转向我硕士论文所处理过的巫觋问题,只是将时代改为六朝,将地理范围限缩于江南。然而,相较于硕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所面对的其实是更为复杂的时空、社会和文化情境。首先,中国的“宗教景观”(landscape of religion)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除了原本的巫觋信仰,这时还多了耀眼夺目的道教和佛教。其次是族群与文化问题,北亚、中亚草原民族不断南移,黄河流域成为胡汉交混的地区,而大量的汉族则向南往长江、珠江流域移动,进入了原本被“中原”视为“蛮野”的荆楚、闽粤文化圈。此外,政治格局也由统一变为分裂,由安定转趋混乱。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巫者与巫俗是否也与时俱变,是否有新的样貌。
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取径和论述策略方面,我也跳脱了硕士论文的老路,视野变宽了,视角也较为多元。这和我在普大的学习及师友的熏陶有关,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一系列有关shamanism的著作研读。我在构思及撰写博士论文时,最让我感到困扰的是一些关键的中文词汇和观念的英译问题,尤其是全文的核心:巫。过去的汉学家或是将巫直接音译为wu,或是译为medium,或是译为shaman。我最后选择了具有争议性的shaman一词,而引发争议的源头是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年)的说法。他认为shaman的语源是通古斯语的saman,基本上是指一种专擅于“出神”或“脱魂”(ecstasy)之技的人,而根据《国语·楚语》的记载,中国巫觋的基本特质却是“降神”(神明降之),也就是所谓的“附身”或“凭灵”(possession),两者虽然都可说是沟通人神(鬼)的灵媒,但通灵的技法与方式却不相同,因此,有不少学者依循埃利亚德的定义,反对将巫觋纳入shamanism的范畴。但是,埃利亚德可能误解了通古斯语中saman的语义。例如,根据专研北亚、东北亚shaman的俄国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1887—1939年)的说法,通古斯saman的主要特质其实和中国的巫觋一样,也是“降神”、“附身”。事实上,西方人类学界反对埃利亚德将“出神”(“脱魂”)视为shaman核心特质的学者还不少。日本学界则采取折中的看法,认为“附身”(“凭灵”)与“出神”(“脱魂”)这两种类型都有,有些社会以“附身”为主,有些社会则以“出神”为主,但也有同时并存者。因此,他们在使用シャーマニズム(shamanism)的时候,通常兼指“附身”与“出神”。事实上,日本的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者,在讨论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一代的巫觋时,绝大多数都会使用シャーマニズム(shamanism)一词,我个人也比较倾向日本学者的用法。除此之外,我还有更坚实的理由使用shaman来翻译巫觋。事实上,南宋徐梦莘(1126—1207年)《三朝北盟会编》便载:“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而珊蛮在清朝时期又常写作萨满、萨蛮,都是saman的音译,而女真语、满语、通古斯语(Tungus language)都同属于阿尔泰语系(Altaic language)。换句话说,将巫与shaman对译的,最晚从宋代就开始了。
无论如何,在阅读各种有关shamanism的论著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开阔了视野。我所处理的虽然是六朝江南的巫觋,但是,我不时会将中国台湾及东南亚、西伯利亚、东北亚,乃至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巫师,或隐或显的作为参照和对应。尤其是当我探讨巫者的鬼神世界和通神方式时,更常仰赖这种全球视野、古今对照和跨域比较,这也是我在硕士的阶段最欠缺的。
其次,在准备“中国宗教”这个科目的学科考试时,我曾阅读不少欧美人类学家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而为了了解他们的立论由来及核心观念,我也进一步看了一些不同流派的人类学经典,这让我充分体会到仪式(ritual)研究对于理解一个宗教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博士论文中特立一章,专论巫者的仪式构成元素、服饰、法器、过程、类型和功能。这也是我过去研究宗教所忽略的面向。
更重要的是,我因此开始比较认真地思考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当时“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cal history)开始蔚为风潮,主要的倡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如勒高夫(J. Le Goff,1924—2014年)、勒华拉杜利(E. Le Roy Ladurie,1929—)等人,但全球各地都有其呼应者。他们或是接受“年鉴学派”的观念,或是和其本地的人类学家展开互动而开创新局。尤其是美国史学家,不仅有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年鉴”的刺激,也有来自美国人类学者如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年)、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年)等人的影响。其中,代表性的史家戴维斯(Natalie Davis,1928—)和丹屯(Robert Darnton,1939—)就任教于普大历史系。或许是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我的写作策略便以“故事”的“叙述”(narrative)为前导,并重视细节的描述。不过,普大的历史学家对我博士论文写作影响较大的,除了余先生之外,其实是史东(Lawrence Stone,1919—1999年),我还采借了他所说的“人群学”(prosopography)概念,将六朝江南的巫者及其信徒视为一种虚拟的“社会群体”,进行分析。
此外,中国的巫者在六朝时期所遭遇的竞争对手,除了士大夫之外,还有新兴的道教和佛教,换句话说,我的博士论文必须处理杨庆堃(1911—1999年)所说的“分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与“组织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在这之间所扮演的角色。这对我是个新的难题,最后是从老一辈的欧洲汉学家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年)、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年)、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年)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等人的著作,获得一些经验。不过,英国史家托马斯(Keith Thomas,1933—)对于英国十六、十七世纪“通俗信仰”(popular belief)的研究,也给了我不少启示。
留学普大,知识的成长主要来自书本。但是,师生的多元背景所汇聚的国际部落,也相当重要。就以东亚系的师生来说,华人之中就有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差异,亚洲各国则有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西洋人除了美国当地之外,还有来自比利时、荷兰、法国、瑞士和英国的。校园中的学术氛围与文化冲撞,经常带给我不小的震撼。

余英时
五、归乡(1994—2001年)
1994年,我通过博士论文口试,取得了学位,返回史语所,展开较长期而稳定的研究工作,并于1995年升等为副研究员,2001年升等为研究员,个人的职等升迁算是相当顺遂。但是,就在这七年之间,台湾的大环境有了激烈的变化,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与重点也因此有了一些转变。这也印证了余先生反复述说的,史学、史家与时代密不可分。
1994年年底,民进党的陈水扁(1950—)在竞选台北市长时,喊出了“台北新故乡”的口号,感动了许多人。我虽然不沾惹政治,但也受到不小的刺激。我是云林人,从高中起就在台北读书、工作,即使扣除当兵、出国的几年,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岁月,已远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可是,我老是觉得家在云林。在台北,像我这样的移居人口非常多,有从台湾中南部来的,有从山地部落来的,也有在1949年从大陆来的,那时候,我们的认同大多还是“祖籍”、“原乡”。阿扁的口号神似东晋南朝的“土断”,提醒许多人要认同当下生活的环境。事实上,那也是台湾“本土化运动”逐渐从政治向社会、文化扩散的关键时期。认识台湾,认识本土蔚为风潮。我也因而投入“北台湾”的宗教研究。
不过,我的“本土”研究其实还是联系着原先的巫觋研究,只是将焦点放在台湾。厉鬼在《周礼》所建构或描述的鬼神体系中并不重要,但“祭厉”一直在中国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六朝时起,厉鬼更成为巫者主要的祭拜对象,而台湾民间庙宇及童乩的主祀神明更是以厉鬼为最主。因此,我以一年的时间,搜罗各种历史资料,并以台北为主,以云林和台南为辅,进行祠庙的田野调查和童乩的仪式观察,最后完成了《孤魂与鬼雄的世界》一书,完整地描述“北台湾”厉鬼信仰的类型、源起、信徒及其与佛、道、巫三者的交涉。我一方面探索这种信仰和汉人文化圈血脉相连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剖析其与台湾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特有的生态、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联。这也可以说是我服膺历史人类学理念的实验之作。
在完成台湾的本土研究之后,我回头省视自己的博士论文,觉得有些课题必须深化讨论。我主要的关怀还是在于厉鬼信仰,因此,便针对“女性人鬼”及蒋子文信仰进行专题研究。其次,为了充分比较各地巫者交通鬼神方式的异同,并强调乐舞在早期中国巫觋仪式中的重要性,我特别以《论衡》所载的“巫叩元弦下死人魂”为切入点,展开较为精细的讨论。再者,由于巫者在许多人类社会中都扮演医疗者的角色,因此,我特别针对六朝时期的巫觋与医疗进行专题研究,并将博士论文中未处理的北朝案例纳入讨论。此外,在我博士论文口试答辩时,余先生曾问我:如何区别巫者和道士?当时我的回答过于简略,论文中也没有完整的讨论,因此,我便借由参加余先生荣退纪念研讨会的机会,在2001年返回普大,宣读《试论六朝时期的道巫之别》一文,算是回答老师当年的质问。
事实上,在这七年之间,我的研究重心并不是巫觋,而是道教史和医疗文化史这两大领域,而且仍然以中国为主要的研究范畴。不过,1997年1月的一趟意外之旅,倒是打破了我原先固守的畛域。那时,我和史语所的同事宋光宇(1949—)以及民族所的张珣一起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进行为期一周的“华人宗教调查”,考察了当地华人的新兴宗教、佛教、民间信仰,同时也访查了童乩的活动。那是我首度接触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教研究,让我对海外华人的世界产生莫大的兴趣。更巧的是,1997年1月23日刚好是印度教的大宝森节(Thaipusan Festival),我们便临时变更行程,加入当地信徒和观光客的行列,搭火车到黑风洞(Batu Caves)的“寺庙洞”(Gua Kuil)朝圣。在途中,我首度看到印度教徒的祈福、赎罪仪式,他们或是戴上“枷锁”(kavadi),或是以长针穿透面颊或舌头,或是以钉钩钉在背部以绳索拖曳“枷锁”。他们有的成群结队,随鼓乐而舞动,神情恍惚,似乎已进入“迷离”(trance)的状态,颇似台湾进香队伍中的童乩,只是很少“流血”。这也让我兴起针对宗教体验和朝圣仪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遗憾的是,这次海外之行所引发的研究兴趣,至今都还没有实践。
六、冒险(2001—2015年)
2001年,在年满四十一岁前,我升等为研究员,同时获得一张聘期到六十五岁的聘书。这意味着我从此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地进行任何课题的研究。我先是重整自己的知识领域和研究版图,以身体史研究统整了我过去的阅读世界和研究成果,找出过去较为硬、实的板块,进行了一些修饰和补强的工作,并将若干论文集结成《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一书。其后,我决定走一条过去不敢走的路,也就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式的专题研究,同时择定了四个课题:一、精魅(妖怪)文化;二、祝由医学;三、槟榔文化;四、巫觋研究。我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能走完全程,看看若干“昔日之芳草”如何变成“今日之萧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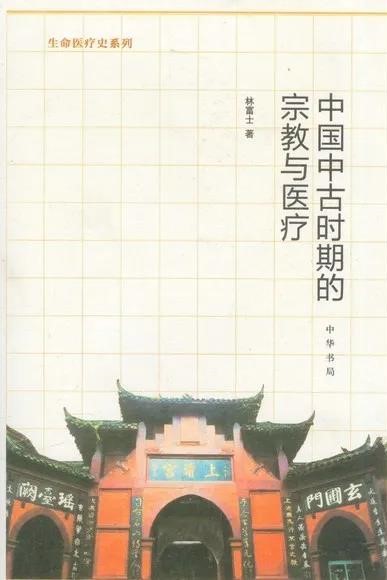
《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
这四个课题的研究都正在开展之中,而我用力最多、耕耘最久、关怀最深的还是巫觋研究。我先是着眼于台湾的童乩,采取历史人类学和人群学的研究取径,除了使用传统文献及各种文字资料之外,还展开一项名为“台湾童乩基本资料”的调查工作,完成大约六百个童乩的初步访谈工作,并长时间在庙会场合进行田野考察,针对“进香”活动和童乩的仪式进行影像拍摄,大约记录了四百位童乩的仪式展演,鲜活地描绘了台湾童乩的面貌。
其次,我转而回归中国的巫觋研究,企图补足过去遗落的环节。我补述了从先秦到两汉巫者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巫者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宋代巫觋信仰的特色。遗憾的是,我仍然未能处理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的巫觋。不过,透过“巫医”传统的考察,我仍然完成了一项贯通性的研究。而在处理“巫医”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在中国古代与中古时期的医疗世界中,卜者与巫、医密不可分,因此,又以专文探讨这个课题,并以此祝庆余先生八十大寿。
在这期间,我也大胆地到“域外”探险。2001年2月,我首度踏上朝鲜半岛,到大田地区进行韩国“巫堂”(巫者)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也相当完整地拍摄、记录了一套丧礼中的“降灵”(牵亡)与“功德”仪式。其后,我分别在2010年7月和2011年3月两度到香港考察传统的庙宇和宗教活动。我希望借此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巫觋信仰。可惜的是,停留的时间都太短暂。而另外一种“域外”探险则是踏入“数位人文学”(Digital Humanity)的领域,希望未来能结合数位科技与人文研究,创造新的研究典范。
七、未央(2015—)
回顾这段进出巫觋世界的历程,突然惊觉青春消逝之迅捷与无情,匆匆之间,竟然已过三十载,我在史语所工作的日子也已占人生的一半。我来自穷乡僻壤,出身寒微之家,所幸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良师益友牵成,才能厕身士林,在学术的王国中开垦自己的乐园。遗憾的是,过去十余年,我未能秉持道家“用志不分”、“守一”之训,不自量力,既想尽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故投身一些公共事务,消磨不少精力;又想驰骋于不同的学术疆域,故兵分多路,同时作战,以致无法在任何单一的领域中出类拔萃。
如今年华已由盛壮步入衰老,心中的惶恐也日益增加。而2014年接获余先生出版的新书《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读后更是让我惆怅、感伤。余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诠释中国从巫觋传统转向礼乐传统的文化意涵,清晰地剖示了古代巫者政治、社会地位滑落的文化脉络。这是我始终不敢,也无法碰触的面向。但我终究必须面对,必须处理在各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或突破时期,巫觋信仰如何调适与变迁。读罢,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慨!因此,我便开始整理旧作,打算以此为基础,继续下一个阶段的探索之旅。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获了李怀宇先生的稿约,便决定将最近十年左右的巫觋研究成果,先行结集出版,其余则俟来日。这样的因缘,也算巧妙。
总之,这本书能够出版,必须感谢李怀宇先生的邀约与安排、苏婉婷小姐的排版与校订,以及史语所同仁长期的鞭策与砥砺。而在我知识的探索之旅中,始终扮演导师角色的杜先生与余先生,更让我永远感怀,他们一逾七十,一过八十,却仍然著述不辍,热情一如往年,也让我不敢怠惰。当然,我还必须感谢内人倪晓容数十年的相知、相惜,从美国普林斯顿的“取经”,到法国巴黎的游学、马来西亚的考察、日本京都的交流与香港的城市访查,她始终是我身边最亲密的伴侣与照护者。最后,谨将此书献给先父林德源(1925—2006年)、先母林吴晚(1929—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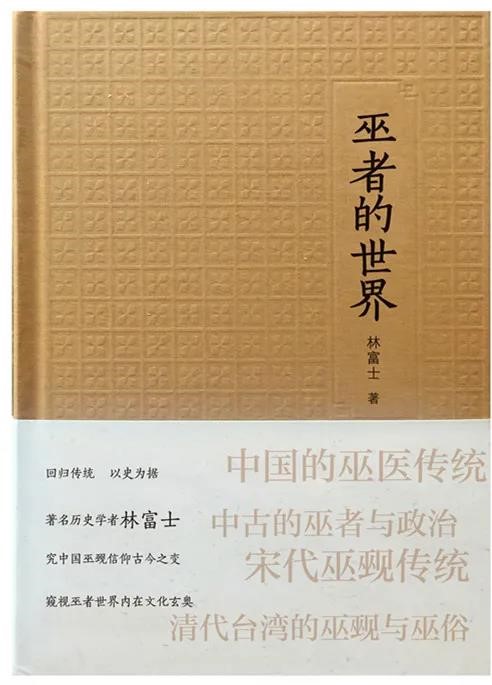
本文系林富士先生为《巫者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撰写的序言,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