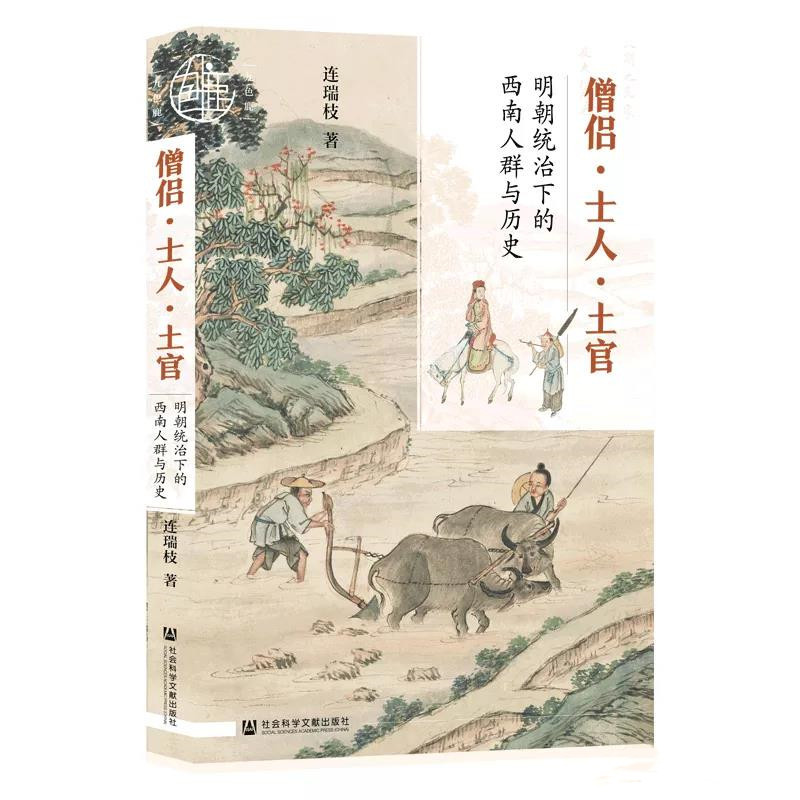
【内容提要】如何安置宗教是中日两国在建设近代国家时碰到的共同难题。本文截取日本的大本教和中国的红卍字会进行比较,指出这两种民间宗教的出现蕴含了对近代的批判意义。不同的是,红卍字会倾向于普遍的社会救济,强调不参与政治,而大本教,自诞生起即有明确的社会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在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从“近代”角度批判大本教和红卍字会的言论,大本教更是遭到了日本帝国政府的弹压。以1923年9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为契机,两个宗教团体迅速走在一起,展开了跨国境的民族主义的合作,但是,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中,它们各自面临着无法超越的现实——近代政治的掣肘。
【关键词】大本教 红卍字会 救济结社 跨国境的民族主义
一、近代/危机
19世纪中叶,东亚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中国和日本相继被卷入全球近代化进程,不同的是,欧美近代国家在实现政教分离后,宗教无论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存在,还是作为社会的存在,依然观照着俗世,而在东亚,如何界定和安置宗教始终是近代国家建设中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日本,明治国家在确立了独尊“国家神道”后,国家权力与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关系依旧暧昧不清,直至大正年间才最终明文化。1919年3月,帝国宗教局颁布法令,规定佛教、基督教及神道十三派之外的信仰团体皆为“类似宗教”——看上去像宗教,实则不是宗教。这样,天理教、金光教等神道教派被归入宗教之列,而大本教等则被视为“类似宗教”。不久,大本教因倡言社会和政治变革,吸引了众多学者、军人加入,导致“类似宗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在晚清中国,严格的僧道管理制度之下,汉地佛教和道教萎靡不振。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在1891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上说:“日本佛教正显示出伟大的觉醒”;中国道教“可悲地堕落了”,“已经萎缩为占卜和驱魔”,“和尚近乎无知和腐败,从中国佛教中看不到复兴的可能性”。与此相对,基督教进入中国,在频遭抵抗后,推进“本土化”,从而获得不少近代知识人的拥护。另一方面,被视为“邪教”的民间信仰及其结社出现了“近代转向”(modern turn),本文所讨论的道院-红卍字会可谓其典型。1922年10月,道院以红卍字会——“社会团体”的名义在北京政府登记备案,从此,道院与红卍字会一体两面,批判近代化带来的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倡言通过内在的修为和外在的慈善拯救社会。在近代与反近代、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碰撞的时代,红卍字会的社会活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关东大地震”。以赈灾为契机,大本教和红卍字会邂逅并建立合作关系,分别在彼此的国家展开活动。对于这段历史,以往鲜有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讨论宗教的近代意义。德国历史理论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批评与危机》一书中指出,“批评”(kritik)与“危机”(krise)具有同样的古希腊语(意为判断、裁判)和拉丁语(意为分开、筛)来源,意思是甄别、判断和决定。作为新宗教团体,大本教和红卍字会的出现及其活动可谓是对“近代”所意涵的“危机”与“批评”两义性反叙事。
二、作为批评的装置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1890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实行为分界点,经历了“文明开化”和日本中心主义两个时代。在明治的“光”和“影”下,社会蠕动着宗教思潮,继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等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京都绫部出现了一个信仰团体——大本教,创教人是名为出口直(“直”一般写作“なお”,音nao,又作直子,1836—1918)的女性。据说是年元旦,这位文盲妇人梦中见到不可思议的光景,第五天夜里发生“降神附体”(神がかり)现象。后来出口直身边的人将其在降神附体时说的话记录下来,称为“笔先”,编辑为大本教的《神谕》。
草创之初的大本教,教义粗糙,多是对其他民间宗教教义的模仿和杂糅,创教六年间一直依托在金光教名下。根据日本权威学者安丸良夫的研究,大本教吸取的其他民间宗教思想具体有三个方面。第一,“创唱宗教”的传统。在江户时代,所有家庭都是特定佛教寺院的檀家,葬仪及相关的死者礼仪皆由僧侣管理。但是,佛教并不能满足民众的信仰要求,于是在降神附体的教祖的提倡下,新的民众“创唱宗教”诞生了,其源流甚至可以上溯到18世纪初。第二,末世论(“终末论”)思想。这里的末世论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末世论,而是基于佛教“弥勒下生”信仰以及日本民间信仰而来的思想,其救世诉求,虽然安丸认为与民众抗争(“一揆”或“世直し”)没有直接关系,但在19世纪80年代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其通过具有“灵威”的教祖或多或少地对民众的思想与行动产生了影响。第三,国家主义的复古神道学说。江户后期以“国学”为中心的神道思想形成,明治维新后“国学”被尊为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其时,国家试图排斥佛教和基督教,在感到无法根除佛教后,于1875年—1976年杜撰了具有宗教特性而又不是宗教的超越佛教各派和教派神道的“国家神道”。明治国家内含体制性的矛盾:基于“文明开化”的要求,明治政府必须要压抑“国学家”和“神道家”所公言的诸神及来世的实在性,缘此,“国学家”和“神道家”的处境非常吊诡,有些人位居国家体制内,有些人则成为国家体制排斥的对象。
出口直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存活8个,这位饱尝人生艰辛的农妇,在“神谕”中表达了对现世的强烈批判:“恶之世”“兽类之世”“利己主义之世”。她声称,这是因为“艮之金神”在三千年(或三千五百年)前被诬为不吉祥,被恶神赶到艮(东北),而恶神自诩善神,必须改变这一善恶颠倒的世界。出口直的这一诉求由其入赘女婿出口王仁三郎所践行和张扬。
出口王仁三郎(1871—1948),原名上田喜三郎,生于距绫部不远的龟冈农村,在贫困与灵修中,年轻的上田喜三郎开始了宗教家的生涯。1899年,上田喜三郎协助山口直创立“金明灵学会”,继承国家主义的复古神道学说,以“镇魂归神法”的神秘体验来证明神的实在性。所谓“镇魂归神法”,就是捕捉游离于身外的“魂”,将其与身统一起来,进入降神附体的状态。神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当将其上升到制约国家乃至世界的层面时,便蕴含了基于现实的危机意识而批判国家和世界的激进色彩。在此,神为切断——“分别”之意,与后文讨论的道院乩坛上的神仙具有同样的功能,这是本文借用科塞雷克“危机”与“批评”言说的原因所在。
1900年,上田喜三郎入赘山口家,与山口直第五个女儿结婚,改名为出口王仁三郎。出口王仁三郎雄心勃勃,意欲从根本上改变偏居乡土的保守的大本教,因而与山口直时常发生意见对立。出口王仁三郎的激进活动引起了警察的关注,在警察的监视和干涉下,出口王仁三郎被迫离开大本教。1908年,出口王仁三郎重回大本教后,成立“大日本修斋会”,将大本教教义释为尊崇“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皇统”,祭神为“以天御中主神、国之常立尊为主的天神地祗八百万神”。安丸认为,出口王仁三郎所阐发的大本教教义居于国家主义的复古神道学说的谱系中,“这一谱系在积极主张神灵的实在性和降神附体上,以及在批判近代文明上,皆与近代日本的正统意识形态相左,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与天皇中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神道保持内在关联的异端,带有将正统意识形态推向极致的性格”,“表面上看完全是国家主义神道团体”,却“隐含了对现实的批判”。与此同时,出口王仁三郎改革大本教组织,从农村迈向都市,大量吸纳著名文化人、军人入教,一些信仰其“镇魂归神法”和“立て替世直し”(改变社会)的信徒甚至变卖财产,举家迁徙到大本教的中心地绫部或龟冈。海军学校教官、英文学者浅野和三郎辞职后移居绫部,主编大本教机关杂志《神灵界》,曾赴中国新疆探险的退役陆军中校日野强携家眷投身大本教,这些人的加入使大本教的面貌焕然一新。
当大本教在日本掀起波澜时,名为道院的新宗教团体在中国山东悄然兴起。据道院文献载,道院兴起于山东滨县。滨县公署后院有一个大仙祠,吸引了周围民众定期前来参拜。约在1915年,滨县驻防营长刘绍基(安徽凤阳人,道名福缘)与县知事吴福森(江苏武进人,道名福永)在大仙祠设乩坛,以扶乩定行止。乩坛的主坛者名为“尚仙”,后被称为“统坛掌籍尚真人”。在开始扶乩时,众人要对尚仙行弟子礼,刘、吴二人的道名即由尚仙所赐。在尚仙的乩坛上,每每出现传说中的神仙和历史人物,这些神仙或人留言于乩坛,给人以启示。从尚仙那里,信众得知最高神是“太乙老人”。日本学者酒井忠夫认为,“太乙老人”一名说明道院信仰源于道家,“是从《老子道德经》中的形而上学——道/自然/无/一等思想脉络中而来的神名,汉代为‘太一’,‘太一’即‘太乙’,而‘老人’一语是将所尊崇的神拟人化。道院的最高神是太乙老人,又曰老祖”,“不能因为道教没有‘老祖’这样的神(名)而说道院不是道教系的宗教”。对此,宗树人(David A. Palmer)根据托名吕洞宾于1917年所作道院经典《太乙北极真经》,推论道院的修为来自先天道的“内丹法”。宫田义矢继袭武内房司关于道院脱胎于同善社的看法,强调《太乙北极真经》实则由“太乙老人”于1920年所作,直接参考了《太乙金华宗旨》和同善社的“内丹法”。笔者认为,20世纪初出现的新宗教虽然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但与以往的民间宗教一样,其思想源流的多元特点一仍其旧。
由刘绍基和吴福森等开启的道院扶乩活动,在道院历史上被称为“滨坛”,只持续了两年。在刘绍基转任济南、吴福森被调往长清县后,道院骨干洪士陶、李振钧等聚集于济南,展开以扶乩为中心的活动,是为“济坛”时代。
济南是山东省会,南北通衢要地,“济坛”面对的是一个与滨县大不相同的世界,名为同善社的新宗教在济南影响甚大。同善社不仅有相对完整的教义、谱系和修行法,还有面向社会的慈善活动,因而对“济坛”的信众产生了吸引力。这促使道院的“济坛”必须改革组织和规范教义。与初期的大本教受惠于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一样,“济坛”在教义上直接从同善社汲取了养分,而地方名流杜秉寅脱离同善社,加入“济坛”,在道院历史上可谓革命性的事件。
杜秉寅取代刘绍基主持“济坛”后,首先规范教义,于1920年开始编纂假托太乙老人之名的《太乙北极真经》,建立众神群仙谱系,试图超越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一般认为,1916年同善社江希张《息战论》所张扬的“五教合一”思想影响了道院,笔者认为似乎没有如此简单,因为在清末民初“五教合一”的思想即已出现,而早期道院文献中关于“五教合一”的主张并不明显。
在组织化方面,杜秉寅利用其人脉关系扩展乩坛的影响,天津的徐世光(道名素一)、济南的何澍(道名素璞)、北京的乔保衡(道名素苞)等各自建立乩坛。1921年春,道院正式成立,年末其外围组织红卍字会成立。1922年10月,红卍字会以慈善团体名义向北京政府内务部申请登记,内务部以“该会章程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旨趣”,予以批准。道院以红卍字会(根据不同情况,本文分别使用“道院”“红卍字会”或”“道院-红卍字会”)获得社会团体的合法性后,利用《哲报》《道德杂志》等刊物宣传,将组织网络向各地扩张。
道院-红卍字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关注,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授林仰山(F. S. Drake)认为道院-红卍字会属于上层阶级(official classes)的组织;金陵大学教授戴籁三(Paul de Witt Twinem)将道院-红卍字会视为与青年学生不同的以旧官僚(older official)、商人(commercial class)为中心的“非基督教运动”(non-Christian movement)的一部分。戴籁三在与南京道院人员交谈时,后者直言不讳地说:“道院针对的是知识人和上层阶级,而教会面对的是无知的下层阶级”。
道院-红卍字会的发展是与其进行的社会救济及整合诸教教义的努力分不开的。1923年4月,杜秉寅突然去世,同年济南道院撰述的《杜默靖先生坐化纪略》回顾道:
辛酉(1921年)春,集合同志创设道院于济南,习静修己,兴慈度人,目击下元之末,浩劫横流,慨然以兴道救世之旨,与同人相勖勉。辛壬两载(1921年—1922年),推设各省各县道院六十余处,并举办红卍字会、道德社、宗教研究会、灵学研究会,与道院相辅而行。至慈善事业,如平民学校、残废院、因利局、栖流工作所以及其他赈灾、施药等事,亦次第设施。……道院之设,精义在融合宗教,使泯后争。
这段文字清楚地道明,道院面向大众所进行的救济活动与调和诸教的努力。确实,在华传教士不约而同地关注道院的“混合性”(syncretism)宗教特质,这和早年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中国宗教的“混合性”(syncrétisme)观察一脉相承。《哲报》刊登了许多涉及宗教调和的文章,这些文章尤其注重与基督徒的对话,这与原为基督徒的清末进士侯延爽关系密切。杜秉寅死后,侯延爽(1871—1942)堪称道院-红卍字会最为活跃的人物,侯延爽对傅斯年的养育之恩常为人所道,其个人事迹则鲜有人知,后文将论及侯延爽与李佳白在济南举行扶乩之事,在李佳白离开济南后,侯延爽又与齐鲁大学艺术与神学院的六名外国人进行了交谈,席间同样展示了扶乩。
关于道院的扶乩,一向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是关注其与明清以来传统的连续性,一是强调二者之间的断裂。笔者认为道院扶乩在形式上毫无疑问继承了以往的传统,内容上则未必尽然,论者对道院所进行的“末世论”的解读似有过之,也无法与本文涉及的大本教的主张相区隔。考察道院的乩文,笔者认为毋宁说道院的主张是一种“衰世论”,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借助“老祖”的灵力来挽救世道沉沦。
载诸《道德杂志》上的乩文,内容驳杂,除调和诸教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道院对社会平等思想及其运动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关,虽曰批判,背后则隐隐显示出“调和”的倾向:“平等二字,纯认为科学物理名词亦可,切不可误认物理名词,括概论理与社会上种种道德原子最为适当”。对于宋教仁的工党主张,“惟希神道之感化,将性灵充满,则操业自精,功修圆明,则乐天成趣,然后以学术道德革新社会,度人于梦醉,庶不致执尊严之谬解,示威行动,为人所利用,蹈其流氓革命,以破坏我将醒之社会也”。在各种乩文中,安庆乩坛上还出现了关于马克思的乩文,乩文道:“世界之杀机,一劫未复,劫劫相乘,抵于无底者,皆溺于国家主义,至死而未悟也。迨及人心厌乱,无法以弭之,遂有社会学说出,脱法令之缚束,就哲理之推敲。思想高尚者,认为天道好还之例,而青年血热者,遂据为英雄造世之功,不惜肝脑涂流,以兴当世”。在“臣民与国主争”“国家与国家争”“社会与国家争”“社会与社会争”,劫劫相复、大启杀机的时代,乩文批评“狭义的社会主义”,倡言:“至于广义的社会学,已无政府之必要,无阶级,无畛域,无门户,无一切障碍”,“吾为误解社会学者示之,光明之路,广大之居,度己而后度人,人人相进而为神,有何国家社会之可言”。
由上可见,大本教与道院-红卍字会形同而实异,在降身附体上,二者有相似之处,都强调通过神秘的体验和启示赋予当下活动以正当性,神仙是判断是非的基准。但是,二者的本质差异也是明显的,在社会批判方面,道院-红卍字会倾向于平等无差的救济,特别强调不涉党派和政治,而大本教,从出口直到出口王仁三郎,社会政治主张不断激进化。在与道院-红卍字会合作后,大本教放弃了批判“唐人”“外国人”的排外主张,但其所谓“人类救善”背后隐含着日本中心主义。就组织而言,大本教仿照红卍字会创立了“人类救善会”,但“救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欲求。相反,道院是坐功修行的场所,红卍字会是慈善组织,如果剥离宗教成分而与近代欧洲的“市民结社”相比较的话,红卍字会毋宁说是一种近代性的“协会”。
三、作为被批评的装置
出口王仁三郎对大本教进行根本改造与其别异的时代感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社会矛盾激化,在“大正民主”思潮下,各种改变社会的主张层出不穷,大本教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及其运动尤其引人注目。对于大本教,帝国政府内务省密切关注,在考虑给予“行政处分”的时机。与此同时,来自日本学界的批判之声始终未曾止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姊崎正治。姊崎正治是日本宗教学的奠基人,1920年9月,他在《变态心理》杂志上撰文批判大本教,指出执着于迷信的人中有很多是“官居高位的知识人”,“即使在社会上或官位上居于高位,即使还有不少知识,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零以下的水平,其中不少人就是我所说的迷信的崇拜者”。他认为,崇拜迷信者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大本教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不如说是来源于如军人这样的“国民一部分(或多数)人的思想”。进而,姊崎反对用谩骂的手法批判大本教,认为应该检讨明治以来日本教育中“科学精神”与“宗教感化”的缺失问题。同年8月,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的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与宗教”系列讲座中,姊崎正治在第二讲后半部分专门从宗教学角度对大本教进行了批判。姊崎正治指出,历史上每逢变动不居的时代,总有一些宗教试图通过“激变”(剧变)和“威吓”等宣扬末世来临,日本当下“最著名的代表是大本教”。大本教信徒的心理状态有共同的特征:不安。在遭遇个人精神莫名其妙的“剧变”之后,有人辞去工作、舍弃财产而投身于大本教。“大本教预言日本受到外国压迫,所谓来自俄国和德国飞机“凡尔登袭击”的心理状态,无论怎样看,都是在期待剧变和威吓,与以战争为业的人需要敌人的心理一样。在追求剧变和威吓上,大本教的心理与军国主义的心理是相通的”。姊崎正治最后指出,大本教宣称出口直的“笔先”预言日本在遭遇袭击后,东京将变成荒野,日本人皆被屠杀,获救的只有位于绫部的大本教。但当这一预言不中时,大本教改口称时间推迟了,再不中,则宣称幸亏我们的祈祷而延期了,最后宣称变革的时间在1921年。
在论及大本教遭到帝国政府第一次弹压的研究中,论者均指责国家滥用权力,鲜有关注1921年之意义者。1921年系辛酉年,《易纬》有“辛酉革命”之说,在日本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大事件。公元900年(昌泰三年),新旧天皇易位不久,右大臣管原道真和左大臣藤原时平之间的争斗趋于激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援引《易纬》,指出次年(901年)正当辛酉,革命在即。10月11日,三善清行上书管原道真称:“天道革命之运,君臣克贼之期”,“明年辛酉,运变当革”,劝管原“知其止足”。管原未加理会,次年被支持藤原时平的醍醐天皇放逐。三善的“辛酉革命”说旨在为打倒权臣管原制造舆论,管原的倒台与其说验证了辛酉革命之不可避免,不如说道出了宫廷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姊崎正治在讲演中痛斥“笔先”内容“重复而令人窒息”,反映了人心中的纠结和不安,反过来唤起了人们意欲变革的狂热。“辛酉年一如三善清行事迹中所载,是阴阳道所谓的革命之年,他们举出这一年乃是希望世上发生剧变”。其时,感到这种“危机”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小岛佑马撰写了长篇论文《儒家与革命思想》,考察儒家语境中的革命话语。
与姊崎正治从宗教学角度展开的大本教批判不同,《变态心理》杂志创办人中村古峡的批判是基于“精神科学”的。兵头晶子认为,“古峡也是灵术界一员之事实说明他的大本教批判是近亲憎恶”。笔者认为,撇开《变态心理》斥责大本教为“迷信”“邪教”等言说,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存在“精神”和“潜意识”,而在于个人的神秘体验——“镇魂归神法”是否可以转换为集体经验并促成社会运动。这也是姊崎正治批判的要点所在。基于这一立场,中村古峡批评“大本教是一个充斥着近乎宗教妄想患者随意涂鸦的偏执狂、妄想型痴呆者、冒险家的集团”。正如姊崎正治所指出的,这是过于偏向“个人心理”的“解剖”,因而陷入了兵头晶子所说的“相克”的境地。对大本教的批判的武器,很快转为武器的批判,1921年2月14日,帝国政府突然取缔大本教,出口王仁三郎以“不敬罪”被捕系狱。
在大本教遭到弹压前后,道院-红卍字会正走出山东一隅,成为受人注目的新宗教慈善团体。一如上文所述,乩坛上诸神群仙的乩文言辞温和,没有渲染“末劫”来临的文字,在围绕修行和慈善的言说中,道院表现出调和诸教的取向。尽管如此,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近代思潮下,道院-红卍字会还是受到了来自近代知识人的质疑。前引《杜默靖先生坐化纪略》有道:
此老祖命设宗教门户,未化之先,欲结绝大慈团以谋救世,不得不暂借乩笔,与世周旋,而求神人感应之效。惟乩赖人扶,不谙内容者,断难无惑,是非速将灵理细为发扬,不足启群众信仰,以达道体借乩之用。此灵学之研究,尤为目前最急之务。默前此屡奉坛训,不知振作,致道之体用,两失其要,思之实多疚心。诸方智慧,率在默上,务望而今而后,各聚精力于此,关乎大道最要最急诸端,悉心筹进。默当随时参与其议,期收实效。果使推行尽则,则道基永固,默亦有荣焉。
“不得不暂借乩笔”,“不谙内容者,断难无惑”等,皆为道院-红卍字会为近代知识人所诟病之处。类似的危机感在《道德杂志》和《哲报》上亦不少见。
近代知识人的批判,以梁启超1922年4月16日在北京哲学社发表的《评非宗教同盟》演讲最为著名。在这次演讲中,梁启超认为宗教是情感性的东西,“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对将信仰作为手段的一切形式的宗教或信仰,梁启超严厉批判道:“我对于那些靠基督肉当面包,靠基督血当红酒的人,对于那些靠释迦牟尼化缘的人,对于那些吃孔教会饭的人,对于那些膜拜吕祖、济癫的人,都深恶痛绝”,“现在弥漫国中的下等宗教——就是我方才说的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么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实在猖獗得很,他的势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几十倍;他的毒害,是经过各个家庭,侵蚀到全国儿童的神圣情感。我们全国多数人在这种信仰状态底下,实在没有颜面和基督教徒争是非”。梁启超认为道院是将信仰作为手段的下层社会的“邪教”,这一判断与事实并不相符。同样对道院-红卍字会持蔑视态度的鲁迅,在1923年1月7日与日本记者橘朴的对话中,虽然嘲笑道院-红卍字会所办“道生银行”的行长是梁启超提到的“吕祖”——吕纯阳,但在橘朴的诘难下,鲁迅承认道院-红卍字会所举办的慈善事业与提倡戒烟戒酒的在理会一样有助于社会。在关于扶乩迷信与慈善事业的关系上,梁启超和鲁迅的态度不大相同,二人虽然均认为神仙降坛是迷信,不仅有害信仰的纯洁性,而且还毒害个人和社会,但鲁迅看到迷信在道德沦丧的时代具有赋予行为——慈善事业以伦理支撑的意义。在批判道院-红卍字会的近代知识人那里能看到这一点的并不多。梁启超在讲演中继续说道:
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复辟派首领打复辟派首领,洪宪派首领、革命派首领、胡匪首领可以聚拢在一起干事;所以和尚庙里头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象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近代性的“信仰”,“信仰”成为工具,政治家利用它,宗教家利用它,而如果没有近代性之信仰,一个国家和国民是无法立足于世界的。显然,梁启超对道院-红卍字会的消息十分留意,演讲中所说“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有迹可寻。原来,就在一个半月前,著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曾专程由北京南下济南道院-红卍字会。2月28日,道院-红卍字会“约在济耶教牧师及各慈善家联一席之欢”。次日,近百人参加了聚会,李佳白和侯延爽先后致辞,并进行了扶乩活动,《道德杂志》录有乩文:
昨耶祖临坛,曾以灵照李子,作一度之言论及之,可知天命。是世界共当恪守之本分,故曰灵体在天有命,散而为世界,无一物不具有此先天之真灵。师曰重灵功就是如爽所言,合耶与谟两教之宗旨。而儒则不从天言命旨者,是为后世有教无宗,而变成第二种形式宗教,舍教以言之大人,一种读是句书,亦可参观大人者,谁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故师重心功,而后佛教倡言明心见性。
坛训中的“李子”即李佳白,“爽”为侯延爽。李佳白回北京后,将上述乩文译为英文后寄至济南《道德杂志》社,《道德杂志》将其附在乩文后刊出。刊出的英文拼写错讹甚多,兹试订正录于下:
Just lately, Jesus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appeared at the altar and by his spirit conveyed this truth to Mr. Ii (Mr. Reid). It must be known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obligation to observe respectfully the Heavenly Decrees. Hence it is said that the spirit originally was in Heaven and had its Decrees, but on its dissemination there is nothing in all the world but that receives this true spirit of primeval Heaven.
The master said: Encourage all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is agrees with the main principle of Jesus and Mohammed. The teaching of the Learned says but little of Heaven and the will of Heaven. Hence, later generation have evolved another form which values education without religion, and which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ult known as the cult of the Great Man, the Man of Power. Reade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Great Man is he who never loses the child heart. Hence, the Master exal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rt, while Buddhists teach that through the clear heart one can see into the nature.
耶稣降坛后,阐释耶教(基督教)和谟教(伊斯兰教)的外在信仰与佛教、儒教的内在修为异曲同工,而这些皆存在于道院所推崇的“五教合一”之中。一如梁启超、鲁迅讥讽扶乩是迷信一样,乩坛上的神仙训示以一种特殊的书写技术呈现人心中的所思所想。在这次扶乩中,乩坛启动后,耶稣降临,书写字画给李佳白,字曰:“古今两圣域,中外一家人”,“春秋知汝,日月其谁”。接着发生书写故障:“耶圣书斜行文数语,以正助纂不娴西文,致乩灵不充,遂改为毛笔书云”,结果不得不以济公译述圣母语的口吻写道:“二纂皆不善英文,多不能随灵伸缩,遗字母处均不免,古文又无译者,欲闻吾灵与欲见吾灵者,就是李子今日所说二字,天命是一个……”而徐光启降坛判云:“耶圣命吾译语诸牧徒曰,吾非不临坛,实真灵与乩坛人灵相接,因乩坛所侍所求者,皆真正良心,默祷之时,故天灵真宰亦随乩灵而动矣,非其事也。”毋庸赘言,无论是历史上的耶稣,还是明代的徐光启,都不谙英文。久居中国,提倡东西融合的李佳白不可能不知道乩坛训示乃是人的作为,但他不道明恰恰是他的高明之处,在他看来,道院是一个宗教慈善组织,宗旨正派,扶乩迷信大可漠视。与李佳白截然不同的是,曾在山东传教的梅特贺士(Medhurst)——自称与王宠惠博士、罗文干先生和复旦大学教授李登辉博士为挚友——特地从国外致信侯延爽,在褒扬道院慈善事业之余,质疑扶乩的合理性,侯延爽不得不进行辩解。
四、无法超越的“近代”
虽然日本史和中国史学者分别研究过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但对二者之间关系知之者并不多。关于大本教,战后日本学界基于对战时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比较关注大本教被弹压的历史;欧美的日本研究者则关注大本教的“超国家主义”思想与天皇制的背反关系。由于大本教的思想和行动含有多重指向,最近有人甚至将大本教的主张视为神道世界主义。在涉及道院-红卍字会的研究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伪满洲国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以及全球化中宗教与世俗的“往还”(traffic)之研究揭示了道院-红卍字会等新宗教的近代意义。与日本民众宗教研究中“救济宗教”一语相呼应,杜赞奇发明的“救世宗教”(redemptive religion)成为研究者广泛使用的概念。确实,“救世”指向不仅使道院-红卍字会获得了“近代性”(modernity)的品格,还呈现出溢出“近代”的特质。本文在此不拟讨论道院-红卍字会“超越性”的思想史意义,将接续杜赞奇提出的超越国境的民族主义话语,透过鲜为人知的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的关系阐释“超越性”中的无法超越的现实:政治。
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分别诞生于日本和中国,各有其源流,在其发展过程中分别受到了近代话语的批判,大本教更是遭到帝国政府的弹压。原本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宗教团体,因为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在日本驻南京领事林出贤次郎的撮合下,迅速走在一起,这一历史的偶然背后蕴含着双方摆脱“危机”的必然性。10月8日,林出贤次郎在致外务省外务大臣伊集院吉彦的函件中提到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要派人到日本赈灾,希望外务省予以帮助。林出贤次郎是大本教徒,目睹大本教的遭遇,试图给大本教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其时,出口王仁三郎被判刑五年,正在取保申诉之中。在社会政治变革的诉求受挫后,大本教徒日野强撰写的畅销书《伊犁纪行》和“大陆浪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出口王仁三郎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帝国膨胀的边境——“满蒙”,因此,对由林出倡议的与道院-红卍字会的合作非常热心。另一方面,林出贤次郎在撮合道院-红卍字会与大本教合作时,并未隐瞒大本教在日本国内的境遇,而道院-红卍字会之所以决定与大本教联手,乃是认为通过赈灾活动可以扩大道院-红卍字会在日本的影响,这与南京的陶保晋和济南的侯延爽不无关系。陶保晋在清末东渡大潮中曾在日本法政大学短期留学。林出贤次郎在南京出入道院,与陶保晋相谈甚欢,在林出的催促下,陶保晋适时地将相关信息上报给北京红卍字会总部,最后总部做出了募捐和派遣赈灾访日团的决定。其间,同样有留学日本经历的侯延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与梅特贺士的辩论中,侯延爽业已透露出在海外发展道院-红卍字会的意图:“近两年来,法之洛诺,德之柏林,意之罗马,美之纽约、旧金山等处,皆有与道院组织相似之融汇各教真理,及研究灵学之会所”。于是,1923年10月初,由侯延爽、冯阅谟和杨承谋三人组成的红卍字会赈灾代表团开始访问日本。赈灾活动结束后,即在京都与出口王仁三郎秘密会晤,确立了大本教与红卍字会的合作关系,于11月21日启程返国。
从1923年10月中日两个新宗教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到1935年12月底大本教遭到帝国政府的毁灭性打击——第二次大本教事件,12年间大本教和道院-红卍字会的合作关系虽然展示了超越近代民族-国家边界的倾向,但最终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对峙的时代,均没有摆脱近代意识形态的掣肘。在与道院-红卍字会建立合作关系后,大本教从试图改变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转向正在膨胀的帝国的边境。1924年2月13日,王仁三郎带领少数随从秘密进入中国,由奉天转入外蒙古,试图在外蒙古建立“光明国”。这次冒险经历记录在王仁三郎自述的《入蒙记》里。这本记录真假难辨,它昭示出大本教在中国北部边陲与游离于帝国政治中心之外的谋求“满蒙独立”的黑龙会建立了联系。而对黑龙会来说,仅靠几个破落王公贵族(如恭亲王)还难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企图,也需要利用大本教与道院-红卍字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找新的代理人。黑龙会的后台头山满和会长山田良平与王仁三郎过从甚密,曾数次出入京都的大本教总部。
在与道院-红卍字会建立关系后,出口王仁三郎仿照其内外互为表里的组织结构,成立了大本教的外围组织“人类救善会”,自此,大本教不再仅仅从日本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来关心日本的未来,而是以“人类”这一话语来关心日本的命运。除中国的道院-红卍字会外,大本教还与朝鲜的普天教、越南的高台教等建立了松散的连带关系。朝鲜业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越南遥不可及,因此与道院-红卍字会才具有超出宗教慈善活动的政治意义。翻阅大本教的报刊和出口王仁三郎的演讲,内里充斥着日本帝国征服世界、大本教一统天下的言辞,大本教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走在了帝国侵略中国的前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本教欢呼帝国的决断,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大本教突然示好红卍字会,请求后者帮助寻找日军士兵的尸体。在日本国内涌动的不安和变革思潮中,大本教成立名为“昭和青年会”的组织,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改变既有的政治格局,发出了姊崎正治所批判的“激变”“威吓”的预言,结果于1935年12月遭到了帝国政府的残酷镇压。受事件的牵连,日本国内的其他“类似宗教”皆遭取缔。
与大本教有目的地利用红卍字会关系网拓展在中国的活动相比,红卍字会还停留在朴素的跨境民族主义和人道关怀上。1924年3月6日,红卍字会在日本神户设立道院,以华侨为活动对象。日本其他地区的所谓红卍字会分会其实只是一张招牌,既没有红卍字会成员,也没有与红卍字会主旨相匹配的活动,均依托在大本教的“人类救善会”上。红卍字会在日本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中国募捐援助日本震灾和其他灾害的受害者,二是断断续续派遣人员访问日本。在红卍字会与大本教的关系上,侯延爽是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此人长期滞留在大本教龟冈总部,充当了大本教与红卍字会之间联络人的角色。红卍字会在沈阳刊刻的《东瀛布道日记》是目前仅见的一本出自红卍字会的实录。
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展开,红卍字会作为一个松散的社会团体,各地分会的境遇各不相同。在东北,红卍字会先被伪满洲国视为“类似宗教”,继而又被归入“教化团体”,迫使其公开宣布与北京总会断绝关系。在道院的乩坛上,甚至还出现了赞美伪满统治的乩文。伴随日本侵华的步伐,从华北到华中,各地红卍字会先后被纳入日军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之中。
五、结语
通过将大本教与道院-红卍字会置于彼此由以生成的语境中进行比较,不难看到,尽管二者的兴起各有不同前提,但还是有一定可比性的,二者都试图借助对过去的重新诠释并预设可期待的未来批判“近代”带来的不安。大本教诞生于明治末年,原本是抵制外来一切思潮的复古新宗教,在大正动荡的时代风潮影响下,转而倡言社会政治变革;在遭到弹压后,又转而面向帝国膨胀的边疆,倡导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是作为有限的近代国家,还是作为广域的帝国,大本教无法在日本近代政治秩序中博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以姊崎正治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对大本教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姊崎及其所要维护的体制并没有对大本教的质疑给出解决的答案。大正时代(1912—1925)日本正经历孤独的帝国主义,以往不曾有过的新的政治可能性隐约可见,但最终未能凸显,代之而来的战争最后将日本送上了破灭之路。可以说,大本教所喊出来的“激变”“威吓”是作为日本近代的反命题出现的,这应验了科塞雷克在《批判与危机》里阐述的一个核心观点,特定的历史意识与所经验的社会危机及其批判有关,它最终是与乌托邦的关于未来的概念发生了联系。
历史的展开充满了变数。就本文的爬梳可知,尽管道院-红卍字会与大本教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组织架构和思想取向完全别异。与日本大正时代大致对应的是中国的北京政府时期,在这一转型期,各种政治思潮竞相呈现,最后汇聚为对未来给出许诺的革命大潮。尽管如此,被近代主义历史叙述屏蔽的道院-红卍字会的思想意义应该予以重视,后者通过诸神临坛——扶乩,批判近代带来的不安,在革命来临之前,近代知识人在展开其批判之时,并没有给不安的时代开出一方安定剂。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主导下,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实行政教分离,战前的“类似宗教”团体获得法律保护而成为“宗教法人”。出狱后的出口王仁三郎转向陶艺,大本教的教务交由其子出口荣二负责。出口荣二倾向于左翼世界和平主义,1962年7月19日在参加莫斯科举办的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后,应中国佛教协会之邀飞抵北京访问,前往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巨赞、周叔迦等。7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出口荣二。7月28日,出口荣二乘机离京前往广州,取道香港回国,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巨赞、周叔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杰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李寿葆等,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到机场送行。次日,《人民日报》报道:“出口荣二先生是本月19日到达北京的,在京期间,除参观访问和游览名胜古迹外,还和我国宗教界人士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大本教领导人来我国访问并和我国宗教界广泛接触,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时,日本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出口荣二回国后不久即在大本教内部的政争中失势。
当大本教浴火重生,战后红卍字会因其在战争下与日伪的“灰色”关系而受到追究。东北红卍字会首当其冲,该会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痛陈附和伪满乃不得已之举。促成大本教与红卍字会合作的陶保晋,因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救助难民而被迫挂名了11天“自治会会长”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镇压反革命和反动会道门的暴风中,红卍字会从大陆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伴随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民间友好代表团的往来日益频繁。在苏州郊外的寒山寺,点缀着数棵樱花树,树下曾立有一枚小牌:笹川良一、出口荣二。出口荣二就是二十年前访问北京的大本教“总长”,笹川良一乃大名鼎鼎的笹川财团的总裁,这位战前在“满蒙”活动,政治上属于右翼的人物,战后致力于中日和解,在当代中国留下了深深足迹,但鲜有人知道战后他曾长期担任日本红卍字会会长之职。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