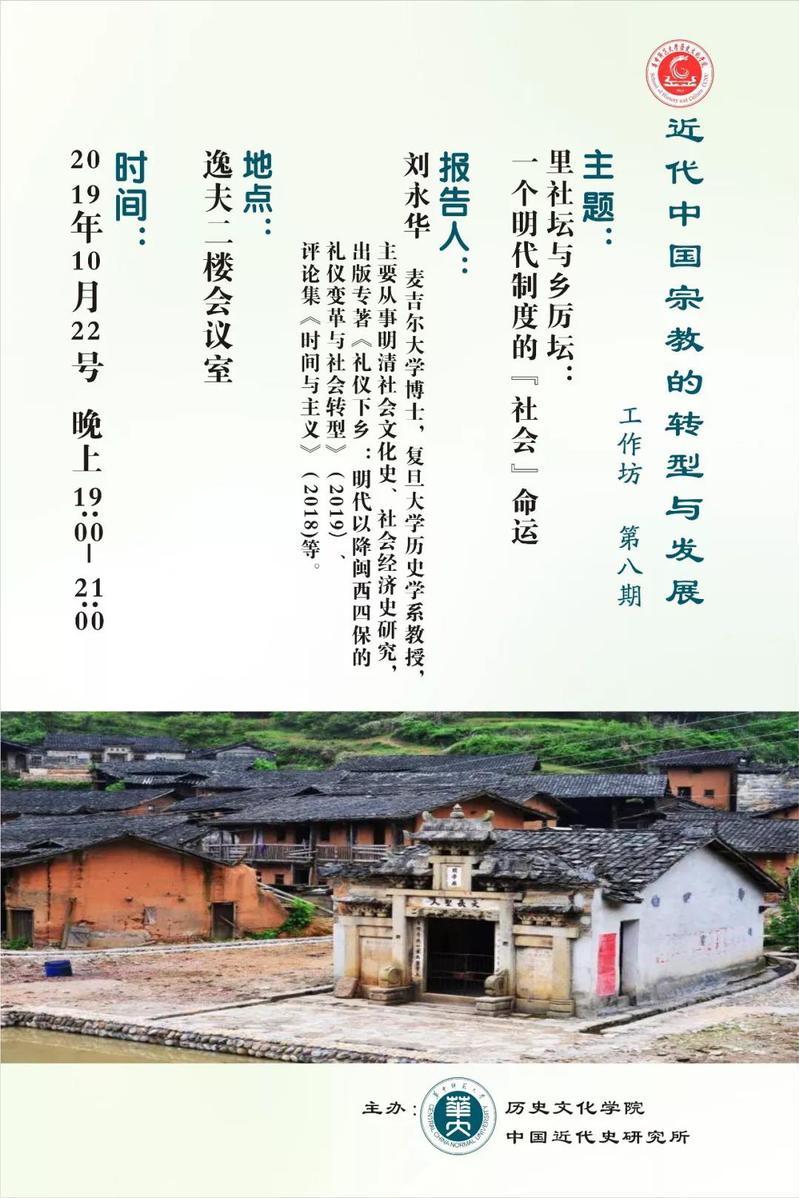
2019年10月22日(周二)晚19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中国宗教的转型与发展”工作坊第八期活动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做了题为“里社坛与乡厉坛:一个明代制度的‘社会’命运”的讲座。本场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付海晏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刘永华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进行了解读。刘教授认为,当前我们所常用的“社会”一词,是在近代从海外引入的。而在中国本土的历史传统中,亦有“社会”一词,只是意涵不同,意为“社之会”,即地域社会。
接着,刘老师谈起了研究缘起。此前,学界对于社坛和厉坛(下文简称“两坛”)已有一定研究。如日本东洋史学者滨岛敦俊教授认为“两坛”在江南地区并未留下太多痕迹,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则对社与庙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刘老师本人在闽西四保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曾注意到田野点附近的“两坛”历史痕迹,遂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究。“两坛”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直到明代洪武年间才通过国家制度推行至乡间。刘永华老师的研究旨在展示出这一“礼化为俗”的过程,是理解王朝礼制与地域社会互动的切面。
明初,《洪武礼制》规定,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同时,从社坛誓词中也可看出,立坛具有抑强扶弱的功能,因而能够推动地域社会建立守望相助的关系。同样地,《洪武礼制》也对厉坛做了规定,使其在国、州、县、乡各级都建立起来。乡间厉坛通过城隍来祭祀“无祀鬼神”,请鬼神保佑良善之家,阴谴恶民恶官。王朝礼制的推行,使两坛在明初普遍建立,但是其在各地的持续时长不一,在明后期又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到了清代,国家层面不再设厉坛,对民间则不作要求,于是州、县、乡层面的厉坛得到了延续
在叙述完两坛的基本情况后,刘老师又从三个维度分析了两坛与地域社会的互动。
其一,仪式-社会体系:在社坛祭祀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矛盾,出现了原本一起祭祀的几个群体分别上报官府,请求“分铸执照”,分开祭祀的情况。于是在乡间又出现了不同层级的社坛,即“分社”。里社坛最多可分为三级。与之类似,厉坛也存在“分厉”的情况。刘老师认为,分社、分厉与聚落的分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两坛”祭祀推动聚落认同的兴起,影响着“社会”与社会的生成与变化。
其二,“民间礼仪”的生成:各地在两坛祭祀过程中,都有属于自己的“礼仪手册”,借以遵循。各地的祭祀过程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如一般都是各家轮流做社,准备祭祀需要的供品;又有特殊性,如祭祀时长(天数)不一。通过对各地“礼仪手册”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民间礼仪制度的了解。
其三,帝国象征:在社坛祭祀过程中,许多地方逐渐出现了“斗法”的旧说传闻。在这些传闻中,斗法双方正是地方人家的先祖与他们所祭祀的社公。各地的旧说颇为相似,以至于可以整理出较为通用的故事结构来。一般来说是:地方人家不堪社公的需索无厌(如要求祭献童男童女),村中某人便到其他地方(如茅山)去学法,然后以法术斗社公,最终打倒社公,或杀死,或驱逐,或使之妥协。从这些故事中的法师形象之中,刘老师看到了道教形象对民间礼仪的影响。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原本社公在王朝礼制中是“丰产之神”的形象,何以演变成需索无厌的邪魔?这似乎象征着帝国形象在乡间的演变,社公很有可能是当地官府的隐喻。

最后,刘老师耐心回答在场师生的提问,并与几位老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撰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潘恩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