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之路——访杨际平先生
一、北朝隋唐《地令》《田令》的研究
问:杨先生好!感谢您接受访谈。杨先生您已80岁高寿,至今仍每天伏案工作七八个小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活力,令后学钦佩。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贡献卓越,均田制是先生的学术研究起点,请您结合治学之路,谈谈均田制的研究缘起。
答: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均田制”是今人的一种习称,我过去也常这么说。后经师友郑学檬提醒:唐代没有“均田制”,只有《田令》。一查,果然如此。北魏隋唐律令确实只讲《地令》《田令》,不说均田制、均田令。隋唐五代时人没有“均田制”“均田令”的提法,唐人皇甫湜的元和三年(808)对策说“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元之际,不授田而均,不名田而赡”,(《文苑英华》卷四八九)更是直截了当地否定唐代有什么均田之制。隋唐五代时人常称《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为“井田事”,如《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即载:户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亦载“(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分理户口、井田之事”。所以近几年我就既不用时人习称之“井田”事,也不用今人习称之“均田制”“均田令”,而迳直称之为《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
唐宋以来,古今学者对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情况的评估就分歧很大。有说“我太宗、元(玄)宗井田法非修也”的;也有说北齐、北周以降,“田皆在官”(《文献通考》卷二“水心叶氏曰”),“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通志》卷六一郑樵语)。今人也是既有言“均田制”为土地国有制的,也有人说“均田制”只是一纸空文的。分歧如此之大,自然很值得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衣凌先生,很注重利用明清时期的契约、族谱、碑刻等民间资料。韩国磐先生研究隋唐史,也大量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两位先生都很注重具有实证特点的出土资料,我个人恰好也比较喜欢利用此类资料。
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厦大图书馆阅览室看到了《敦煌资料》第一辑,便深深地被它所吸引,认为这是研究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遂决定据此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
1980年奉韩国磐先生之命,与李伯重同学至社科院历史所拜会熊德基先生,始有幸获阅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大喜过望,遂复印而归。《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所收相关资料较之《敦煌资料》更为丰富、准确,遂成为我此后硕士论文《略论均田制的几个问题》的主要参考资料。研究生毕业后,我仍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并持续参加讨论。
问:在20世纪,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日学者又是怎么围绕北魏隋唐《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进行讨论的?
答: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学者对敦煌文书和早先从吐鲁番带回,藏于龙谷大学的大谷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研究走在中国前头。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吐鲁番晋—唐近400座墓葬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其出土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的陆续出版,与北京图书馆唐耕耦、陆宏基整理编辑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的陆续出版,情况发生逆转,中国学者对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研究后来居上。
中日学者关于《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争论,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形成以铃本俊为代表的土地还授否定说与以仁井田陞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两种对立观点。铃木俊等通过对敦煌户籍资料的系统研究,认为:其时“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别无非是户籍的记载形式。换言之,户籍上出现的土地关系就是对农民的现有土地,以永业田为基础,套用均田条文。如果某户的所有地多于规定的永业田额时,就将其中的一部分按规定当作永业田,再把其余地当作口分田”,因而否定土地还授的实施。仁井田陞主要依据唐代敦煌户籍的田亩四至中有“退田”字样,大谷文书中又有“还公”“死退”“剩退”等字样,因而认为不能否定唐代实行了土地还授。由于铃木俊等的研究,论据很坚实,所以得到包括中国学者(如邓广铭、杨志玖等)在内的多数学者的认同。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日本学者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系统整理并研究了大谷退田文书、欠田文书、给田文书,认为这些文书就是唐代西州(即吐鲁番地区)实行土地还授的确证,从而大大加强了土地还授肯定说。大谷欠田文书、给田文书,应授田的标准是一丁10亩(常田四亩,三易部田六亩),与《唐令·田令》的规定明显不合。西村元佑解释说“户籍所示的应受田额,是作为公示天下的大原则的令制的基准,在这个大原则范围之内,还存在着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作为因地而异的实施细则的‘式’的基准。西州一丁10亩的基准额,恐怕就是西州地方行政细则中规定的”,开元时期,吐鲁番地区就是依此“受田基准额”进行切实的土地还受。吐鲁番如此,敦煌等地亦如此。虽然也有学者,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怀疑欠田、退田、给田文书不是均田制的土地还授,而是屯田的土地还授,但无确证。因为大谷退田文书、欠田文书、给田文书中确有大量的土地还授实例;由于唐令《田令》与《户部式》等皆不存,《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亦尚未出版,人们一时也尚难对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的假设提出强有力的驳论,所以一时几成定论,连原先持土地还授否定说的铃木俊、池田温也改变主意,承认唐代西州厉行了土地还授,只是认为这是吐鲁番地区的特殊现象。
第三阶段就是戴建国等据宋《天圣令》所附《唐令》完整复原《唐令·田令》以后至今。
问:学术界关于《地令》《田令》的讨论聚讼纷纷,杨老师是如何进一步展开《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研究工作的呢?
答: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地令》《田令》实施状况讨论时,以西嶋定生、西村元佑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正风靡一时,中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说可成定论,再无置喙余地。我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的。我将《唐令·田令》实施情况问题分解成8个方面:1.隋唐时期是否有“被公认的私有土地”?2.初授田时,平民百姓是否普遍实授土地?3.官吏是否普遍实授土地?4.寺观是否普遍实授土地?5.土地还授时通常是户内帐面调整,还是实际还授?6.《唐令·田令》在抑制土地兼并时起什么作用?7.《唐令·田令》之下是否还有各地因地而异的“受田基准额”?8.西村元佑、西嶋定生等借以立论的大谷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所反映的土地还授,是在“均田制”之内,还是在“均田制”之外?每个小问题都力图从传世文献记载、敦煌出土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每一个主要论点都有充分的、可靠的论据作支撑,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西嶋定生曾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唐代曾存在一种不包括在均田制之内而叫做‘自田’的公认的私有地。这个意见很重要。如果这个意见正确,那么,无论是否认还是肯定唐朝实施均田制的人,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同时又不加任何论证,迳直认定大谷欠田、给田、退田诸文书就是当时“均田制”下的土地还授,并进而推论:即使在一般内地也切实进行班田收授。
针对西嶋定生、西村元佑上述观点,我写了三篇与之商榷的长文:《从唐代敦煌户籍资料看均田制下私田的存在——兼与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教授商榷》(《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4期)、《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兼与日本学者西村元佑、西嶋定生先生商榷》,(《唐史论丛》第1辑)、《唐代西州欠田、退田、给田诸文书非均田说补证——兼论唐代西州两种授田制度》(载韩国磐先生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惜皆未见到回应。
随着天一阁藏本宋《天圣令·田令》所附《唐令·田令》的发现与完整复原,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唐令·田令》第34条就规定:“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限满之日,所借人口分未足者,官田即听充口分,若当县受田悉足者,年限虽满,亦不在追限。应得永业者,听充永业,私田不合……”。《唐律》本身就有“诸盗耕种公、私田”“诸妄认公、私田”“诸在官侵夺私田”等条文,而敦煌吐鲁番户籍的田亩四至连接中也可以发现许多各户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有地。唐代曾存在一种不包括在《田令》制度设计之内的公认的私有地,已经无庸置疑,以西嶋定生、西村元佑为代表的土地还授肯定说,确实“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观点”。
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计56条共4000多字,其中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者约占40%。完整复原后的《唐令·田令》既有原则规定,又有很具体的实施细则,不容也不可能再有“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作为因地而异的实施细则的‘式’的基准”。西嶋定生、西村元佑等的假设,乃想当然的向壁虚构,完全不合历史事实。《吐鲁番出土文书》(4—10册)也充分证明:唐代西州确实存在两种授田制度:一种是《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狭乡每丁应授田60亩;另一种是根据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的《巡抚高昌诏》:“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载《文馆词林》卷六六四),一丁合受常部田十亩。大谷欠田文书、退田文书、给田等文书所反映了正是唐太宗《巡抚高昌诏》所规定的“官田给百姓”。官田给百姓那种授田制度的田土来源,一是废屯,一是内迁户的土地。两种授田制不仅应受田对象、应受田额、文书制作手续与田土分布情况等等方面都迥然不同,而且户籍登记的形式也不同,两者互不兼容。
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原本就有:各户“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规定;土地还受之际,本身就有户内帐面调整规定。土地还受否定说者从敦煌吐鲁番户籍资料归纳出来的许多规律性认识,都从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中得到强有力的印证。
问:杨先生可否谈谈对北朝隋唐《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的总体认识?
答:北魏隋唐《地令》《田令》都既有给无地或少地农民授田规定,同时也都有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各户已受田的,亦即不触动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都既有进丁授田,入老或身死退田规定,同时又有“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家内人别减分”或“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的户内帐面调整规定。所授之地,北魏明确限于“听逐空荒”与绝户田,唐代则仅限于公荒废地。就民户可能因此得到部分公荒废地这一点而言,《地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垦荒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限田制度;就其明文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土地还授之际先在户内进行调整而言,它实际上又只是一种土地登记制度。
北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太和九年(485)初颁《地令》时,首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一带地广人稀,早先曾对迁来的“新民”实行“计口授田”,河西一带因河西大牧场的废弃,也有田可授,因而估计颁布《地令》之初曾在一些地方有过实际授田迹象,但多数地方仍是按《地令》规定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已受田,或者是以买田入籍算作已受田。初授田之后的土地还受,因各地“空荒之地”与“绝户田”拨充职分田后毕竟十分有限,所以基本上还是按《地令》规定“家内人别减分”,实际上无还无受。北周、北齐、隋唐,大体都是如此。武德、贞观年间的少林寺碑与贞观十四年九月(即唐征服高昌的第二个月)李石住、安苦延等户手实等都证明,早在唐初,《唐令·田令》规定的所谓授田就已有名无实。建中元年(780)实施两税法后,《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的结局,因相关户籍资料皆未见而不详。既有可能一仍其旧,继续将各户原有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也有可能从此不了了之。在此之前,北朝隋唐《地令》《唐令》在鼓励垦田与限制土地兼并方面都还是起到一定作用。
问:目前,北朝隋唐《地令》《田令》实施状况的讨论显得很冷清,是否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题无剩意?无须再进行讨论了?
答: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十来年,有关《田令》实施情况的讨论虽显沉寂,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戴建国等先生完整复原《唐令·田令》后,我曾郑重指出,传世文献对《唐令·田令》的介绍很片面,因而许多历史教材与著作介绍唐《田令》时也很片面。现在《唐令·田令》既已完整复原,对《田令》的介绍理应有所改进。很遗憾,近见几部高校历史教材,介绍《唐令·田令》时,还是只讲授田,不讲《唐令·田令》规定的“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只讲土地还授,闭口不讲《唐令·田令》本来就有“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规定,继续误导读者。
近来虽再未见有人撰文论证《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曾被切实实行,但常见学者说,中唐以后,“均田制”如何破坏。言下之意是中唐以前,《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曾被切实实行过。可见,中唐以前,《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是否曾被切实实行,其实施状况如何?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两税法实行后,各地户籍手实是否仍继续按《田令》规定登记其田土,更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建中元年以后唐代户籍手实资料皆不存。在未见到建中以后的唐户籍、手实前,恐难断定两税法实施时《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已经破坏或者说已经崩溃。
二、汉唐赋役制度的研究

问:户调制作为汉唐时期重要的赋役制度,请您谈一下关于户调制起源问题的看法。
答:这和我参加郑学檬先生主持的《中国赋役制度史》的编写工作有关,租调制这部分基本上是我写的。秦汉以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经历三大阶段,从秦汉时期的田租口赋制,到东汉建安九年(204)开始实行的的田租户调制,再到中唐建中元年(780)开始实施的两税法。户调制如何产生?是学界很关注的问题。唐长孺先生对此有过研究,指出魏晋的户调制由两汉的财政调度演变而来。韩国磐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杨小甦的学位论文也曾以《户调探源》(1988)为题,讨论户调制的起源。杨小甦指出:汉代财政调度源于两汉政府财政收入与国家消费的内容在实物形态上的不平衡与各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的不平衡。汉代政府收入的主要是钱与谷,而其消费则主要是谷与帛,这其中的矛盾即使在国家财政收支总量上富有盈余时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调度来解决。各地区物产不同,财政收支情况也不平衡,也需要调有余以补不足。“调”经历了从反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单纯的财政调拨关系到反映政府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的变化。正常的财政调度有严格的制度,通常是由地方政府或部门提出申请,经财政主管部门(如大司农)审核,然后下达。以政府库藏的钱向盛产绢帛的地区市买买绢帛,然后再通过财政调度调拨到需要绢帛的地区。盛产绢帛的地方,每年都有调绢帛的定额。这种财政调度实际上只是政府调拨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库藏以供给国用,反映的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涉及郡国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与赋税制度本身并无直接关系。郡国行政系统或均输系统市布帛(或其他实物)以应调,与地方政府以租谷、赋钱应调一样所反映的都只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是政府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郡国行政系统或均输系统市布帛(或其他实物)以应调,与地方政府以租谷、赋钱应调一样所反映的都只是国家在地区和部门间平衡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一种财政关系,而不是政府与编户齐民之间的赋税关系。倘若政府财政困难,无钱市买绢帛时,情况就不同了。当朝廷下达调发任务,而地方政府既无物可调又无钱市买调物时,解决办法通常有三:1.保留市买形式而贳贷于民。2.中央政府下令加征赋税或由地方政府加征民钱以应调。3.直接向民户摊派调物。后两种方式就是横调、杂赋敛。所谓贳贷于民,通常也是贷而不还。上述这些征敛方式虽然都具有强制性、无偿性,但还没有确定的税则、确定的征税对象,以及全国统一的税额或税率,所以也都还不具有正式赋税的基本特征。在财政持续入不敷出情况下,久而久之,临时性的横调、杂赋敛就逐渐演变的正式的税。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袁氏势力,夺取袁氏地盘后,便正式实行田租户调制,将原先的口钱、算赋与横调、杂赋敛,归并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制正式成立。(以上内容参见《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出土了10多万枚三国吴简,先期披露的一些吴简,涉及到“调”,引起学者的热烈的讨论。或认为其时孙吴的税制还是田租口赋制,或认为当时孙吴已经实行了户调制。2003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2006年我利用该书资料撰文《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调”——兼谈户调制的起源》,在杨小甦观点的基础上,进而认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的“调”布,既非正式的户调制,也不是橫调、杂赋敛,而是政府购买,属正常财政调试范畴。“调”皮则有一部分属于橫调、杂赋敛,通过加征百姓税钱予以支付。
问:唐代租庸调制下江南折租造布的问题引起学者极大的兴趣,也曾成为隋唐财政制度源出东晋南朝说的重要立论依据。那么,我们如何以唐代财政调配的视野来理解唐玄宗时期江南折租造布的现象呢?
答:陈寅恪先生说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江南的折租为布为“南朝旧制”,并由此得出唐中央财政制度渐次南朝化的结论。陈寅恪先生南朝有折租为布制度,所依据的是两条明显失校的南齐资料。其实,南齐并无折租为布制度。《南齐书》卷三《武帝纪》载永明四年(486)“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同书卷四〇《竟陵王子良传》亦记“诏折租布二分取钱”。我以为这两条资料的“租”都是“调”字之误。理由很多,最关键的是上引《南齐书·武帝纪》有“三分之二取见布”句,这个“见”字很重要,在古代就是“现”字,“见布”的意思是该税种的本色是布。租调制时代,租的本色是粮食,只有户调的本色是布。可见上述两则资料的“租”字都是“调”字之误。都是讲折布为钱,而不是折租为布。也就是说南朝本无折租为布制度。既然南朝本无折租为布制度,那么,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就不是什么“南朝旧制”,也就无所谓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问题。开元廿五年前后,江南的折租为布,关内诸州的庸调资课折粟米,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州的折租造绢,通水利州则依旧纳见粮。这么安排,都是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财政调度的成本(主要是运输成本),保证财政供应。中国古代财政制度大致包含四方面的内容:1.财政收入制度(包括赋役制度等);2.财政支出制度;3.财政平衡、财政调度;4.财政管理制度。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并未引起唐代财政收入制度(包括赋役制度)、财政支出制度与财政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动,其所关涉者主要只是财政调度关系。因此说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只不过是唐代财政制度体系中的财政调度这一环节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局部变化而已,算不上是国家财政制度史上之一大变革。
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径与展望
问:杨先生您在做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之间的关系?
答:我做经济史研究的体会是要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资料,既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这两类资料各有不同特点。传世文献有关政治活动与人物活动的记载多,反映社会基层生产生活的少。出土资料则相反,反映社会基层生产生活的多,反映社会上层与朝廷活动的就极少。传世文献往往比较宏观,出土资料一般比较微观。传世文献主观上就是要传世,往往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情感,融入个人偏见,因而容易失真。出土文书本不想传世,就事论事,因此比较客观,带有原始档案性质。两者适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如果只看出土资料,往往背景不清。只看传世文献,往往欠具体,缺乏实证性。所以一定两者互补才行。
研究出土文书,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人侧重研究文书本身,为他人提供方便。有的人则力求利用出土文书,研究社会制度或重大事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都有学术贡献。我个人则比较偏好于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某种经济制度。
上世纪中叶以前,关注出土文书的学者还不很多,有许多学者对出土文书不了解,甚至不以为然。这些年随着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的大量出土,秦国史、孙吴史的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年轻学者多数都很关注出土资料,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践行。
问:您认为青年人怎样才能练好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基本功?
答: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经济史尤其是这样,没有多少主观想象的空间。我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首先是要多看一些原始的经济史资料书,比如《通典》、《唐会要》中就有很多经济史资料,《宋会要辑稿》中的资料就更丰富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肯定都要参考它。至于研究方法这倒没有很专门的书,吴承明先生曾经说过:各种经济理论对我们来说都只是方法论,这也有“史无定法”的含义。只要你的研究在广度、深度上比前人有所推进,能使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什么方法都可用。反之,如果只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用新的概念体系或某种框架加以重新包装,那就没有什么价值。
我个人体会要多看学术争论的文章,围绕着一些争论性的话题,对双方的观点、所使用的材料都认真琢磨,这样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当然这对初学者来说可能有点难,可能觉得争论各方的文章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看多了,思考多了,慢慢就能弄清论战双方分歧所在,哪些提法可以成立,哪些提法不能成立?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
再有,做某项专题研究,要尽量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如研究铁器工具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就得学些冶金史的知识,了解生铁、熟铁、钢铁的性能及其冶炼特点,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深入,在研究过程中才能够发现深层次的问题。
问:杨先生在做经济史研究时,使用了大量图表来呈现自己的论证,请您谈谈对量化研究的看法。
答: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必须掌握充分的相关资料。讨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举出一两个例证,这比较容易,但往往不能说明问题。因为相反的例证可能举出更多。例证自然越多越好,但例证多了,就不能简单罗列,就要考虑用制作图表或用统计的方法加以利用。先许多年,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曾来厦大参加研究生答辩,他就说厦大研究经济史,很喜欢用图表。事实也是如此。我觉得,算出来的结论往往比举例式的结论更有说服力。量化和图表的方法可以容纳大量资料,包涵大量的信息。比如我在研究敦煌吐鲁番地区租佃关系时,就把一百多件契约中的信息归纳在图表中,定额租,分成租,货币地租,分别有多少件,亩租多少,租期多长,一目了然。
问:作为资深的经济史研究学者,请您为当前的研究提些批评性意见或者建议?
答:早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曾经有一个偏向就是比较重视法令规定,忽视其实施状况的考察。这一情况现在有了很大改善。现在的一个缺点是很多学者做学问前后贯通不够。老一辈史学家都强调前后贯通,现在的基本倾向是每个人的研究时段越来越短,多数仅局限于一个断代。甚至仅局限于一个断代的某一侧面。对前后断代既不关心,也不甚了了,却又喜欢妄加褒贬,做“比较研究”。近见几篇宋史论文,谈宋代租佃关系的发展,说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是我国封建土地制度演进史上的一方醒目的路标,说以人身依附关系淡化为标志的租佃关系的发展都生在、长在北宋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这块土壤里,说中唐以前是部曲庄园制。这几位学者显然不了解前面提到的1981年—199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先后出版,其文书的年代都在中唐以前。该出土文书中户籍手实甚多,其中提及一些部曲,但数量极少,因而唐史学者普遍认为唐代部曲几近绝迹,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该出土文书还表明唐代租佃关系、契约租佃关系都很盛行,租佃制已明显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该出土文书中的租佃契,仅唐前期的多达60多件(不算唐代以前的约40件),而目前所见的宋、辽、金、元直至明初的租佃契却总共不超过30件。可见这几位宋史学者笔下的唐代,与唐代现实相差有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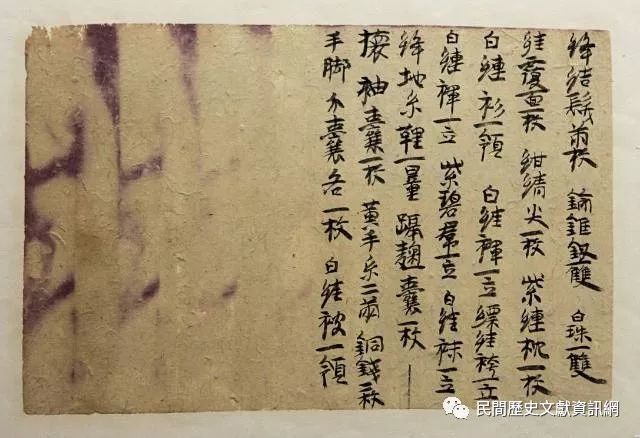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重点研究某个时段某一方面,这没问题,但至少要瞻前顾后。前后断代的书不可能都读,但泛读几本,哪怕只是翻翻,还是有好处的。“略知一二”,总比浑然不知好。
当前更大的问题是做经济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前半段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转移到了其他时段或者其他领域。并不是说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济史研究没有什么潜力可挖,其实,深入研究可话,可以讨论的问题还很多。虽然做经济史研究难度很大,但真正坐下去,也不会感到很难,也会乐在其中,我退休了依然在做经济史研究,就是因为乐在其中。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廈門大學歷史系趙永磊、卓競採訪整理。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3期,第55-65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